文:岳鸿飞
现居香港的艺术史学家韦一空把他对本地当代艺术高度个人化的叙述命名为“我爱香港”,这原本是香港六十年代本土英语流行组合“夜明珠合唱团”的名曲《香港九龙》里的一句歌词。无论是基调还是研究角度,韦一空都采取了和阿克巴阿巴斯不同的处理方法。后者的论述中充满焦躁的后殖民悲观主义情绪,其“文化消失”的概念对回归时期美学焦虑做出了高度批判的解读,对后来的文化生产和评价产生了极大影响。而《我爱香港》则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生动的多元文化主义怀着深刻的喜爱,偏向欧陆理论,并坚持建立在地区层面上的具体实在的世界主义。这里面并非所有东西都有效,但也不失为催生珠三角地区文化生产积极问题意识的建设性一步。尽管文字围绕若干重要概念展开,但韦一空主要还是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逸闻趣事,为他在当代艺术领域里的体验以及所做的解读勾勒出一幅虽不规整但令人愉快的图景。以画家周俊辉为例,他出现在有关克里斯蒂娃和普鲁斯特的一页以及提到王兴伟和王庆松的段落之间;“本土化的散居者”这一概念通过对拉康和巴特的标准解读得以呈现,两者加在一起颇具说服力地阐明了香港社会生活中内在的多语(英语、粤语、普通话)切换现象;北京胡同、沙田沥源桥、十九世纪法国建筑师维欧勒勒杜克的遗迹保护工作三者间的对比结合来自周蕾的批评理论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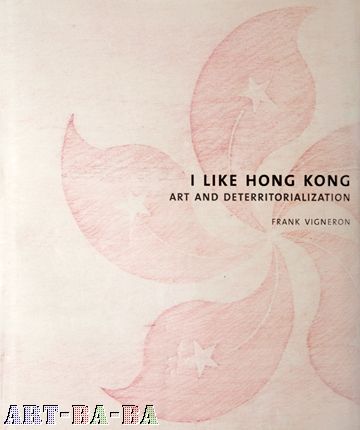
韦一空,《我爱香港:艺术与去域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315页,英文
这本书也许没有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对香港艺术进行连贯、系统的整理归纳,但至少表明一种在全球理论和美学进展影响下的泛珠三角叙述是可行,而且可能的。《我爱香港》试图书写一段香港艺术的历史,在承认中国当代艺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注意不让自己完全陷入大陆意识的逻辑。尽管韦一空并不反对大陆的做法,但他主要还是为香港辩护,所谓辩护也并不立足本土优越感,而是指他在分析作品时倾向于忽视其中的瑕疵和怪癖。对中国大陆艺术家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部分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但韦一空并未提出这个令人不快的系统性问题,而是选择把关尚智和海波这样的艺术家放到一起讨论我们不禁怀疑,对这种并置,可能两位艺术家都要表示反对吧。韦一空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但正如本书主题分类以及作者对艺术家分组和时间表过于随意的处理所示,《我爱香港》无疑应归为一本艺术评论集。但作者也直接表明了“主观”价值评判的拒绝,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己书写历史的权利。他不愿接受现有的一套名字和作品划分规范,因为提出规范的香港展览体系本身就已经够弱小了,算来算去,这个体系里只有一座名存实亡的美术馆、近亲繁殖的大学学院以及若干未经质疑的私人画廊。
现居香港的艺术史学家韦一空把他对本地当代艺术高度个人化的叙述命名为“我爱香港”,这原本是香港六十年代本土英语流行组合“夜明珠合唱团”的名曲《香港九龙》里的一句歌词。无论是基调还是研究角度,韦一空都采取了和阿克巴阿巴斯不同的处理方法。后者的论述中充满焦躁的后殖民悲观主义情绪,其“文化消失”的概念对回归时期美学焦虑做出了高度批判的解读,对后来的文化生产和评价产生了极大影响。而《我爱香港》则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生动的多元文化主义怀着深刻的喜爱,偏向欧陆理论,并坚持建立在地区层面上的具体实在的世界主义。这里面并非所有东西都有效,但也不失为催生珠三角地区文化生产积极问题意识的建设性一步。尽管文字围绕若干重要概念展开,但韦一空主要还是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逸闻趣事,为他在当代艺术领域里的体验以及所做的解读勾勒出一幅虽不规整但令人愉快的图景。以画家周俊辉为例,他出现在有关克里斯蒂娃和普鲁斯特的一页以及提到王兴伟和王庆松的段落之间;“本土化的散居者”这一概念通过对拉康和巴特的标准解读得以呈现,两者加在一起颇具说服力地阐明了香港社会生活中内在的多语(英语、粤语、普通话)切换现象;北京胡同、沙田沥源桥、十九世纪法国建筑师维欧勒勒杜克的遗迹保护工作三者间的对比结合来自周蕾的批评理论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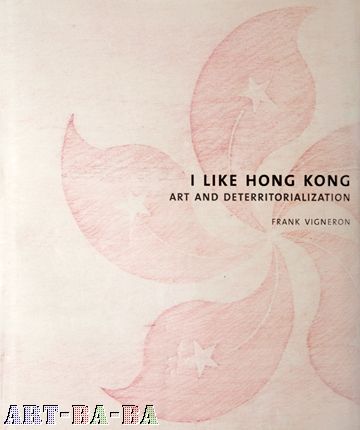
韦一空,《我爱香港:艺术与去域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315页,英文
这本书也许没有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对香港艺术进行连贯、系统的整理归纳,但至少表明一种在全球理论和美学进展影响下的泛珠三角叙述是可行,而且可能的。《我爱香港》试图书写一段香港艺术的历史,在承认中国当代艺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注意不让自己完全陷入大陆意识的逻辑。尽管韦一空并不反对大陆的做法,但他主要还是为香港辩护,所谓辩护也并不立足本土优越感,而是指他在分析作品时倾向于忽视其中的瑕疵和怪癖。对中国大陆艺术家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部分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但韦一空并未提出这个令人不快的系统性问题,而是选择把关尚智和海波这样的艺术家放到一起讨论我们不禁怀疑,对这种并置,可能两位艺术家都要表示反对吧。韦一空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但正如本书主题分类以及作者对艺术家分组和时间表过于随意的处理所示,《我爱香港》无疑应归为一本艺术评论集。但作者也直接表明了“主观”价值评判的拒绝,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己书写历史的权利。他不愿接受现有的一套名字和作品划分规范,因为提出规范的香港展览体系本身就已经够弱小了,算来算去,这个体系里只有一座名存实亡的美术馆、近亲繁殖的大学学院以及若干未经质疑的私人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