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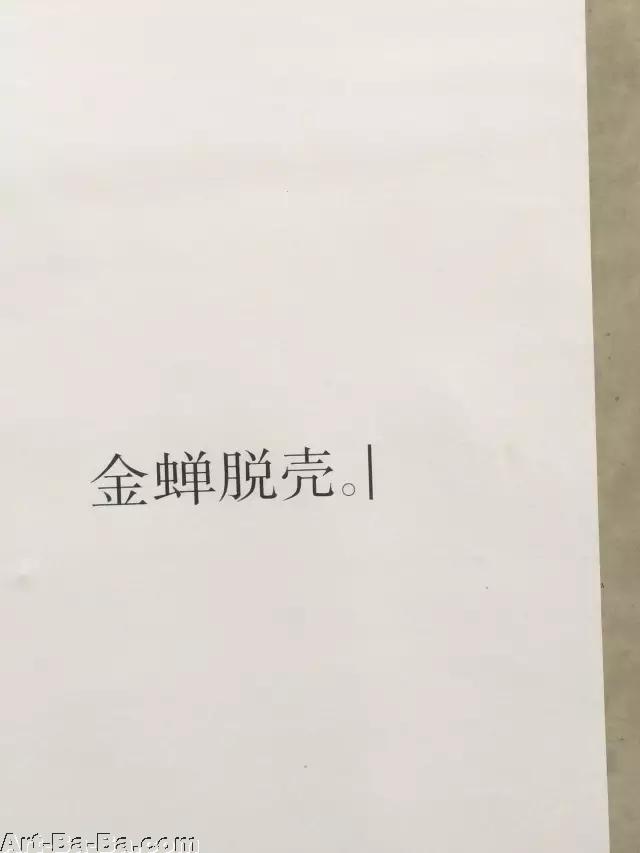
黄专老师的思想与行动,影响到了他周围很多人,我应当是被那种氛围吸引、并受其影响的其中一位。从OCAT到华山村的那条路,那些人与事,在这座追逐效率和金钱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当时的OCAT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公司,更像是一个同仁团队。那应当是OCAT最好的时期。我对OCAT的评论,既是基于一名记者的职业本份和自觉,也有维护我心中的那个“乌托邦”的私心,这些文章给黄专老师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他给予的是宽容和鼓励,还送了我一支派克钢笔,激励我继续写下去。
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都能感受到黄专老师对晚辈的帮助和提携,虽然接触不算少,但与黄专老师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交谈,这是我至今都很遗憾的地方,开始做《打边炉》时,就计划等到他身体好转了,到祈福做一个采访,哪知医学的奇迹没有再一次发生。《打边炉》自2015年4月开始,在征得黄专老师的许可,陆续发布了几篇他的文章,这些文章影响了我,并且是常读常新,今天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重新整理出来,我相信对于一名写作者而言,重读,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钟刚
什么人算是批评家?

在我的印象中下列五类分子不宜算批评家:
1、为体制利益服务或随时准备为体制利益服务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2、以谋利为写作和工作目的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3、没有一些可靠的专业本领(如语言、写作、鉴赏、逻辑等等)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4、自认为既是艺术家又是批评家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5、导师、领袖、先知一类的人不宜算批评家。
……
我不是批评家,不仅因为我不够格,而且因为我一直将我在九十年代以来所干的一些有限的工作视为一种 “社会测试”,而不是“批评”: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是测试艺术对商业体制的反应能力;1996年的“学术邀请展”是测试艺术审查制度与艺术合法性的关系;1997年的“何香凝美术馆学术论坛”是测试艺术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学科关系;1994年到1996年间策划改版《画廊》是测试公共传媒与艺术的关系;1999年的“雕塑年度展”是测试艺术与公共化的可能性……这些测试尽管失败的居多,但往好里想,它们或许多少为当代艺术在本土环境的自由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教训。或者说,为真正的批评提供了一些材料。坦白地说,我对艺术发生和生产条件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某个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流派的兴趣,这也注定使我成不了批评家。
摘自《黄专:什么人算是批评家?》(《打边炉》2015年03月25日推送,原文发表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00年第01期)
当代何以成史?

当代何以成史,现在也许首先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一种学问态度和价值判断问题。我们无法回到艺术单一标准的时代(譬如以“征服自然”或“美”作为目标的时代),而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艺术史的原则,当前历史的写作就无法进行。在我看来,这些原则首先应该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譬如,“当红”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标准,而那些有持续的问题意识、创造逻辑和思维智慧的艺术家才应该是故事的主角;另外,我们应该回到以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为中心的写作上来,它的意思是:我们除了要耐心了解形成艺术家思维模式的环境和逻辑外,还必须对构成艺术家成就的最主要方面,他的特殊的视觉方法和技术成分进行描述,而不能仅仅满足对各种新奇观念的解释和标签式的定位。其次,如果你是对历史而不是对时尚感兴趣,你就还应该去了解形成这个时代的艺术生态和情境逻辑的基本线索,在繁杂的资讯和信息背后(我们可以称它为史料)机敏地发现哪些是会对我们的文化真正产生影响的问题,而哪些只是出名的把戏,最后,要做到上面这一点除了必备的史学修养和强烈的历史感觉外,你还必须做一些诸如编年、史料甄别一类的基础工作,当然,最后,你还应当适当地克制对艺术进行过度的文化和诗学阐释的冲动。
摘自《黄专:当代何以成史》,《打边炉》2015年5月18日推送。该文为《走自己的路: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家》“代编者序”。
如何理解“独立”

“独立”是一个很空泛的词,就像“民主”和“自由”一样。但对于我来说,建立机构,“独立”是一个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OCAT建立以后,何香凝美术馆和华侨城还是给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OCAT的理念和项目设计很少受到干扰和制约。当时提出这个口号,主要考虑的还是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问题。
2005年前后,中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充分的国际化,但这种国际化是建立在西方展览制度和遴选机制上的,缺乏一个独立的自我解释和研究机制,所以OCAT成立之后,它所做的项目主要是本土艺术家的项目,虽然它也与国外同类机构进行了广泛的联络,但利用OCAT这个平台,形成一套独立的自我批评和研究机制是它的主要动因,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所谓替代空间实践吧,当时强调“独立”主要还是针对这方面。另外,当时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艺术的充分资本化,除了拍卖或市场,还有传媒,上世纪90年代还没有电子传媒,所以当时的纸媒还有很大的独立性。21世纪以后,传媒与资本已有了很密切的共谋关系,而很多私人或企业投资的美术馆大多数也已成为变相性的资本运作空间,这也是当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OCAT也是直接由企业赞助,如何处理独立机构与企业利益的关系,这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幸运的是,我坦率地提出OCAT的性质不是企业美术馆,而是企业资助的独立艺术机构,机构项目与企业商业活动脱勾,这些都得到了华侨城的认可,我想这是我这么多年来能和他们合作的一个基础,当然,同时我也会考虑OCAT给企业带来的社会回报和收藏回报。总之,对于OCAT来说,“独立”可能显得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最后,“独立”其实也是针对我个人的,要通过展览、研究、出版体现自己独立的学术立场,在这样一个小型机构中把自己的判断能力展示出来。所以,强调独立也是一个自我要求。另外,我也希望培养OCAT这个团队的独立性,它首先体现在人格上的独立,团队的每个成员,无论是日常工作、项目设计,还是对外部交流,我都希望在团队有独立讨论和相互批评的氛围,我觉得能不能在一个小的范围形成这个机制是机构保持独立的前提,独立性不是一种简单的姿态,强调机构内部形成既充分独立又充分协作的工作关系也是“独立”的重要内容。
摘录自《黄专:在独立艺术机构实践中寻找自己的逻辑》,《打边炉》2016年4月20日推送。采访收录至《OCAT十年:理念、实践与文献》一书(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为什么要抵制成为公众人物?

因为成为公众人物你就不能按你的思想来说话啊,那样的话,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我而言,不能按自己想的去说是件特别难受的事情。我做个展览,杂志要采访那我没办法。因为你做了事情你不能装清高,好像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但我是尽量避免,做了事,大家怎么看、怎么评论都行,没必要自己再去说什么。中国现在很多文化人在传媒上很有名气了,成了公众人物以后,他自然而就放弃了很多东西,真的是,连他说话的方式甚至性格都会变的,你看他在电视上说话的神情举止啊,那种夸张的口吻,我觉得那是被传媒逼出来的,这的确是一件很要命的事。
摘自《问黄专→为什么你要抵制成为公众人物?》,《打边炉》2016年3月8日推送,作者谢湘南,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并收录至黄专文集《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
OCAT怎样选择艺术家?

选择机制从OCAT的学术架构设计就可以看出,首先,他们的创作和中国这30年的历史有关系。我不会选择一个突然红起来的艺术家,这就是根据我刚才讲的历史研究的原则。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历史,就不会进入我的选择的范围。第二,他/她的作品必须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这个问题又有很高的普适性。它不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也应该与国际性问题相关,这也是一个标准。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一辈子都做好作品,但是他/她的作品必须是有自己的逻辑,有共性化的问题,有通过自己的创造改变环境的可能性。当然,建立研究合作的默契也很重要。
我曾说过,中国能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在我看来也就只有二十来位。这当然是个玩笑话,但在我的心里其实有一个名单,不过我在OCAT也只是做了七年,策划了七个艺术家的项目,可能就是这个名单的三分之一。如果我把这个名单全部做完,也许就是一部我们书写的历史。不过,这里有很多向项目都需要机缘,需要资金,我们的研究能力和资金其实是不足以完成这些项目的。我也不能说这七个项目就能够包括我自己的选择机制,但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的条件基础下,也只能做到这样了。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要批评这些项目,这些批评我都可以接受。这些年通过对艺术家的研究,我发现,我们的艺术家从基本文献到研究其实还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巫鸿写王广义文章,感叹地说:你连1980年代的作品名称都没法确定,我怎么可能去研究你?所以做这件事情,起点就是要从最基本的事情开始,把每件作品的名称、时间弄清楚,从最基本的著录工作开始,我们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在西方,这种基础的研究机制也许早就形成了,甚至二、三流艺术家都有这样的研究基础。中国的选择机制要么是个人好恶,要么是意识形态,要么是市场,中国艺术家的拍卖纪录、展览纪录通常比他们作品本身的信息精准得多,这的确是很可悲的。
摘录自《黄专:在独立艺术机构实践中寻找自己的逻辑》,《打边炉》2016年4月20日推送。采访收录至《OCAT十年:理念、实践与文献》一书(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OCAT为什么要建立馆群?

OCAT艺术馆群的缘起有些偶然,在2011年6月的一次馆长办公会议上,武汉华侨城提出在他们营销空间建一个美术馆以配合他们的营销活动做些展览,其实当时在成都、北京的华侨城也都在做些以艺术展览名义的营销活动,甚至挂了OCAT的名。在会上任总提出能不能在各地的华侨城都建立OCAT?这个提议得到了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总裁陈剑的响应。在这个会议上我并没有表态,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严格来讲,把美术馆和企业营销活动结合这与建立OCAT的初衷是不符的。但是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各地华侨城办展览不通过我们,直接挂OCAT的名,甚至以OCAT的名义聘请策划人、收藏作品,我们也没有任何法律或行政手段限制他们,所以他们说,与其放任,不如规范。应该说,这是建立馆群的一个初衷,并不是OCAT的一个最开始的设想,应该说,它是一个被动的选择。
后来我提交了一个关于馆群的计划。原则上希望各地馆群和深圳OCAT一样,保持它作为独立艺术机构的性质,由企业提供资金赞助,OCAT指定执行馆长作为专业策划人,而且强调了OCAT并没有为企业做营销活动的义务。馆群计划设计了两套班子:第一套是理事会,由投资方组成,主要负责资金投入和整体行政、人事的管理;第二套是学术委员会,是专业决策机制,OCAT在学术上的独立性就是靠学术委员会这个机制。2012年OCAT正式注册成为一个民营美术馆,OCAT自然就从何香凝美术馆独立出来。
建立OCAT艺术馆群,好处是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OCAT这个模式的延续,而且获得了更为稳定的资金投入,局限是各地华侨城的投入热情、资金状况不同,企业管理方式和思维方式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美术馆的工作性质和效率。现在很多问题都在磨合中,如何进入到一种良性发展现在还很难判断。
摘录自《黄专:在独立艺术机构实践中寻找自己的逻辑》,《打边炉》2016年4月20日推送。采访收录至《OCAT十年:理念、实践与文献》一书(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中国当代艺术最缺什么?

它缺乏的实际上是思想性!也就是说,你怎么思维一个问题?因为人类的所有创造都是思想导致的,那么,这个思想是怎么来的?这个思想的构成方式在艺术创作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元素?这个思想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很高深或是很深刻的思想,甚至是“我要卖好画”,这也是一种思想,因为如果要卖好画的话,还需要找到不同的对象。有的是为了一种表达,不考虑其他的,那么,这种表达是如何表达的?还有的是想和阅读或者其他的知识发生关系,思想不仅仅是思想的表达和陈述,它还包括思想的语境、遭遇、对话、形状和延续,所有的这些我都叫做“思想性”。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缺乏思想性呢?它缺乏一种思维的逻辑,缺乏一种对一件事情的判断逻辑。很简单,我们看到杜尚,我们就想到他声名显赫又臭名昭著的《小便池》,想到《小便池》又会简单将它归为达达,这就把杜尚给简单化了。所以说,一个思想在接受一个信息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简单化或者歪曲化。这一次王广义的展览就邀请了一位杜尚的好朋友阿图罗·斯沃茨(Arturo Schwarz),他也是达达的研究专家,他就和我聊,因为是杜尚几十年的好朋友,他也参加了这次的研讨会,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谈到通过什么途径理解杜尚的问题,比如《大玻璃》(或《被男人剥光衣服的新娘》)这件比小便器重要得多的作品我们有没有真正介绍过?这其实是一个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展开的问题。在中国的出版物其实就只有《杜尚的谈话录》,当然,如果有大量关于杜尚的出版物,那本谈话录可能会变成很好的文本,但是如果只有它,那么,它很可能就变成我们更加曲解杜尚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次他就把他研究杜尚的最后一个文本留给了我,而且他当场就写了授权书。
我想,我们的思想性也离不开历史意识和语境,所以,如果我们有可能把杜尚的翻译和研究,作为中国重新认识当代艺术的一个起点,比如说,杜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波伊斯(Joseph Beuys)也是,每个人都在说波伊斯,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波伊斯?所以,我也把这一部分作为我们下一步要建立的历史框架的问题。当然,因为我个人没有外语,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有另外一位具有这种历史意识和历史立场的人来做这件事情,我现在也在物色合适的人选。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基础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作,中国艺术家的思想永远很肤浅,很稀薄,很没有逻辑,这些过程其实都是相关的。当时范景中很有运气,他有一批当时愿意投入帮他进行翻译或者选择文本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要建立这样一批人,在中国的大学里是不可能了,在中国的公立的美术馆也不可能,所以,我们也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来做事情,这也是我所想做的事情。
摘自《“历史是一种捕捉”——黄专谈OCAT的出版项目》,《打边炉》2016年4月28日推送。节选自《OCAT十年:理念、实践与文献》一书。
大病后为什么要“追求功名”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喜欢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沉思默想的学者生活和活跃进取的功名生活孰优孰劣。我不知道这类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无意义,但我总觉得在这两者间也许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兼容,事实上,正是在这两者间某种程度的张力也许才是智慧和思想生存的最适度的温床,所以我常用“行动的沉思”来解释自己的选择,在我看来,行动并不是思想的确证或反映,相反,思想只有在进入到行动中时才具有逻辑上的可能,当然,在这里,行动可以是社会行为、可以是艺术创作,也可以是一种自主性的写作……
2001年的一场大病后我就一直在揣摩上天的意图,在我的很多善意的朋友和敌意者看来我仍选择了一种追求功名的世俗生活简直匪夷所思,而我自己则还是希望把这种选择看成一种独特的沉思默想,在我看来,这种行动性的思考与其说是在探求真理,不如说是对各种确然性真理的怀疑和冒犯,它只是一种个人性的生活方式,一种无法解释和无须解释的“雾中的自由”(昆德拉语)。最近我为张晓刚的艺术写了点东西,这不是为了学术,也不是为了和他的友谊,而是为了自己,为了某种灵魂的救赎,在这篇文章中我把他称为“自述性个人主义”以区别于“道德性自由主义”,我一生都在讨厌和怀疑那些把自己打扮成道德主义的人,在我看来他们的毛病不仅在于伪善而且在于说谎,而这篇东西只在赞扬艺术中最基本和最高贵的一种品质:自由的思想,它想证明:它们可以是伟才雄辩,也可以是喃喃低语。
摘自《黄专:只有思想是重要的》(《打边炉》2015年4月23日推送,该文是《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