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来画廊
关于流水线项目
顾灵:今天来了不少广州的朋友,还有你原来广美的同学。你回到广州来,会觉得亲切吗?
李消非:对,现在来广州,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美院刚毕业那时,我是迫切地要离开这里。其实当时我在广州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我一门心思只想做艺术家,所以去上海找了一个教师的工作。我还记得特别有意思,我和那时候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妻子郭庆玲,在美院附近的地摊上一人买了一件类似盖世太保的走私皮衣,广州一年到头都很热,穿皮衣的机会不多。后来我去了上海,郭庆玲穿着这件皮衣去找工作面试,没通过,隔了好多年才知道,当时是因为她穿那件皮衣实在太酷,面试的领导担心以后管不住这么有个性的人,就没敢要,哈哈。
顾灵:嗯,所以现在创作里制造业、工厂的题材和广州的城市背景没什么关系?
李消非:毕业之后主要是画画,和这个创作主题没什么关系,但你知道我一直对秩序很着迷,也是可以从录像的画面里看出来的。拍工厂最开始是2010年策展人汪单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公共艺术项目,是上海地铁里的灯箱。我当时采访了一些不同阶层的人,从采访里选出一句话配上照片做成海报。受访的人中就有一个印刷工人,他在谈起他的生活和工作时,无意识流露出与他年龄不太相称的复杂情绪,非常吸引我,于是想去他工作的现场了解更多。之后我就去了他工作的车间拍摄了一些现场素材,结合他的采访,剪辑完成了流水线项目的第一个录像作品《一个印刷工人》。后来就一发不可收,那段时间我的朋友们看到我都怕了,因为我逢人就问有没有工厂可以去拍。然后也就陆陆续续有了《一个车间主任》,《一个外企老板》等等。“流水线”这个名字,因为2012年林白丽邀我在OV画廊做个展,需要一个名字作为展览标题,当时也没多想。后来作品越来越多,慢慢就形成了“流水线项目”的概念。到现在,一共有一百多部了,分成了“访谈系列、无声系列、日常系列”,使用的媒介还有装置、图片、综合材料等。2015年初,我成立了流水线项目工作室,希望能与不同学科的人进行合作,不定期地策划和组织系列主题活动。

成绩决定一切 灯箱,300cm×150cm,2010(非展览作品)
顾灵:这也是近年来的一种趋势,比如李龙雨和小汉斯做的“上海种子”就号称要打造一个跨学科的平台,不仅是知识上的交流,还提供不同视角和思考方式的碰撞。尤其你的作品在关注的话题上又是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的。
李消非:2015年流水线项目工作室策划了两个展览,第一个展览的主题是“有保障,很稳定。”第二个主题是“希腾电子”。我们邀请了诗人、哲学家、电影导演、人类学者、民间剧场团体和其他艺术小组参入展览,虽然不是深度的合作,但我们是用一种开放的姿态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来探索与之相关联和延伸的“流水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现在很多的信息与视角的来源主要是电影,以前多看经典,现在看得更泛一些。
顾灵:看电影会潜移默化地转换成你剪接时的直觉经验。
李消非:这是一方面,主要是影响我的思维方式,怎样多角度地分析时间、空间和叙事的问题。
顾灵:所以可以说下你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是如何处理这些素材吗,把哪些东西留下来,把哪些东西剪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你有很多很多的硬盘,里面装满了上千小时的拍摄素材,但最终成片大多只有十几分钟。
李消非:通常我会把刚拍完的素材放一段时间,做冷处理,就是说让这些素材看起来很陌生,好像不是自己拍的,过一段时间再去剪辑。最初素材拍好后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后来我想其实人跟机器是一种完全平行的关系,有时交错在一起,我试着用切片的方式—人、机器,人、机器穿插在一起,将人与机器相互重组和转换,以达到一种平行、交错的关系。影像的节奏非常快,在初期的“访谈系列”中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那时自己感觉效果不错,就一直这样拍下来了,形式上慢慢的也多了一些。到现在七年的时间,跑了很多地方,也拍摄了大量素材。现在想想,真不容易,拍了160多家工厂,国内外都有。所有走访过的这些工厂都需要动用很多的社会关系才能去拍摄。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工作,当然前期都是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各种朋友的关系。后来也尝试过别的方式,比如微博、微信、找学校的老师、学生等,但好像效果并不太好,我自己感觉最管用的还是找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现在我最希望在工厂拍摄的状态是像工人一样在车间工作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他的语言会随着你的想法改变 Audio / Color / HD / PAL / 08'45'',尺寸可变,2010(非展览作品)
顾灵:所以进入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感觉?找画面?
李消非:很难去概括,去的多了就会慢慢有一种观察方式,包括方向与方法。流水线项目有很多作品系列,最早是录像的“访谈系列”,注重机器的一些局部和画面感,至于人本身,尽可能不去拍。然后到“无声系列”只截取一些局部来拍,把上下关系去掉。到了“日常系列”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人、机器、环境这样的关系,慢慢减弱机器占主体的影像关系。去年年底的作品《崇明岛》主要是拍女工在工作间隙发呆的状态,上周我再一次去到这个工厂的时候,镜头开始慢慢往下移,拍工人的腰部、臀部、鞋子以及身体姿态,拍到后来我自己感觉好像有些无聊,但拍摄的过程中还是非常兴奋的。
回头想想,2013年的《一包盐》是我的一个转折点,开始脱离只是车间这一个范围,重新考虑人以及人背后的一些故事和环境。到去年拍摄《沙发》的时候,我开始植入一些场景到现场里,有意地去干预它,使影像既具有现实性,又存在着虚幻的意味。比如在家具厂的鹅毛车间,我请朋友在镜头看不见的地方吹鹅毛,让本来就在填充鹅毛时飞舞的鹅毛飞得更厉害。在拍《崇明岛》之前,我很少去拍工人的心理反应,《崇明岛》里有一个女工一直在凝视着镜头,我自己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是能感受到自己在与她对话,其实现场的关系并不是这样。在现场,我是尽可能的让工人忽略摄像机的存在,以获取一种最真实的、最自然的现场。

沙发(视频截图) HD Video / PAL / Color / Sound / 13'47",尺寸可变,2017

崇明岛(视频截图) HD Video / PAL / Color / Sound / 10'30",尺寸可变,2017
顾灵:所以后期的时候不需要把前期的素材都看一遍。
李消非:不需要,我对我拍过的东西基本还有印象的。这里面有一种关于真实与虚幻的关系,这是我自己个人特有的一种感受,别人很难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不是亲历者。
顾灵:所以现在你能做到曾经拍的各种素材再调用出来,你自己是有一个作品的索引,现在展出的时候也会重新调用之前作品。
李消非:不同展览会有不同的考虑,如3月初在西安OCAT的个展和4月下旬在纽约的个展,以及在本来画廊的展览,我都是根据不同空间来选择作品。这次在画廊的展览“无声系列”的作品全都静音,是考虑到这个现场的空间和其他作品之间不合适太强的声音。但同时我还是希望将多个现场平行立体的同时展示出来,另外我也特别注重展览现场的节奏感。如:在西安OCAT的布展是采用一个凹型的方式,因西安OCAT的底层空间特别完整,而且足够大,所以用三面环绕的方式,每一面四个录像,每个录像的屏幕尺寸是4米x2.25米,每一面一个“日常系列”的作品做为主屏(有一个独立的声音罩),其他三个为“无声系列”的作品,有时有声音有时没有声音,现场能感觉到主次和节奏,观众可以坐下来看完整个作品也可以随时离开。
顾灵:装置本身与影像创作之间会不会形成一种什么关系?还是相对独立的?
李消非:装置作品会考虑与展览现场的关系,与影像的创作思路有些不一样。现在可以将不同的录像作品与装置作品进行排列组合,每个影像配合一个装置和其他作品。

展览现场
我不排除任何呈现的方式
顾灵:谈谈绘画本身的东西,你好像对秩序性的东西有一种迷恋。
李消非:之前也提及毕业的时候就画过一些机器,本身我自己性格也是比较有条理,逻辑性也稍强一点,像《未知域》这个作品感觉好像有一种强迫症,但我去现场看到那些有秩序性的画面会特别兴奋。我在2015年曾经在一家工厂做过一个行为,是帮工厂按照我的意思整理仓库,打扫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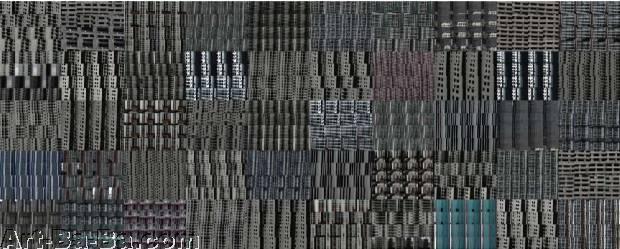
与之相对应的标准-02 照片,80×200cm,2006
顾灵:在你的作品中还是能体会到一种绘画的质感,也可能与你在油画系毕业相关。美学上的作为视觉艺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绘画有其自己的的逻辑,它是如何转换到影像艺术中呈现的?包括色彩上的质感上的光线上的,像你之前说的,相对来说这些影像的调子是比较灰的,但相对来说这反而是特别真实的状态。
李消非:我的作品全部都降调了,这源于现场的感受,以及我自己认识到这种真实就是这个样子,甚至比这个再灰暗一点。我要的那种感觉是看起来是像黑白片,但回过头来想,其实发现是有颜色的。关于画面感如何去把控,这个实际上很难说出一种方法,只有在面对现场那一瞬间做出一个决定。
顾灵:剪辑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种高强度的关注的状态,这在你作品中的体现就是一种长时间的专注的凝视,把瞬时的凝视拉长的时间感被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个绘画中长久的观看传统是有关的。你赋予画面一个延长的时间,创造出来一个关注的观看空间,这是一种剪辑上的手法,但也是呼应长时间观看一个画面的凝视状态。
李消非:当我拍摄一个女工在监测香烟过滤纸的场景时,我只选取了很少的一个部分,类似这样局部、瞬间的场景我拍过很多,它们看起来很像一幅幅古典油画,但放在展览现场感觉特别虚幻和荒谬。

流水线No.01(视频截图) HD Video / PAL /Color / Sound / 5'25",尺寸可变,2012(非展览作品)
顾灵:所以以前说的心理感受可以拆分出一些相对具体的,时间感是相对具体的感受,像工人在十几个小时在做重复的动作,以及他们在工作间歇稍作休息的状态,这两种时间感形成的对比是不一样的,而这些画面给拍摄的人以及观看的人的时间感又是不一样的。
李消非:是的,像刚刚我说的,最近我开始拍工人的下半身,如:脚、鞋……我感觉自己很无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拍了,但他们的这些细节和姿势已经说明一切,双脚前后的关系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劳作。
顾灵:你说的要筹备一个电影长度的作品,可能在结构上的要求更高,但你不会去给他一个脚本,更多的是考虑前后素材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方法与绘画的方法是呼应的。你几乎完全不去思考影视专业的工作方法,还是在延续一种传统的,绘画式的工作方法。那我们再来谈谈这次有点回归架上意味的《程序》这件作品?
李消非:这些是工人炼银时需要做的工序,他们需要将这些材料折叠多次,然后进行电解,我把它简化成五次工序,以前我是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现在我采用平面的方式将这些瞬间定格下来。
顾灵:所以你也不排除从动态的影像回归到静态的绘画、装置中。
李消非:我不排除任何的呈现方式,包括这次对谈,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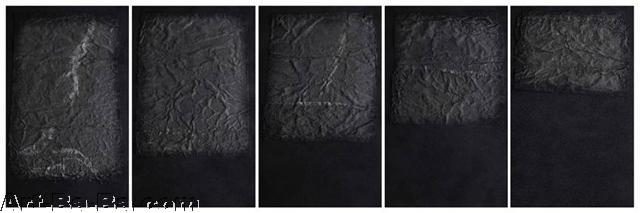
程序1号 银片、铅片、清漆、铁粉,85×52cm (5pcs),2017
如果我的作品是在诉苦,那是非常失败的
顾灵:你的录像作品在拍摄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距离感,是不是进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逐渐有了用工厂中的东西做作品的想法?
李消非:我从小就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每次在工厂看到那些半成品的材料,我就特别喜欢,比如在浦东的一个铜管厂,我看到在拉伸的那些未成形的铜管,被绕成巨大的圆圈,悬吊在偌大的车间中,那样的现场让我特别的震撼,很自然就有一种把现场做出来的冲动。
顾灵:是不是这里有很强的控制性,像无序的状态变成有序的状态,没有形态的东西变成强调形态的东西。而工厂又是强化这种强制性,强调有序性为效率服务的环境。走了这么多的工厂,工厂本身运作的的逻辑甚至是哲学性的关系,工厂对整个工作过程的控制,是否是你的作品想要传达的东西?
李消非:你说的这些其实在进入工厂的瞬间就全部暴露出来,无论大小的工厂。我去过一些超大工厂,可以说一个工厂就是整个城市。5月初我去挪威、芬兰、俄罗斯交接的尼克尔(Nikel)考察,尼克尔这个城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污染非常严重,那里主要是生产“镍”,这是一种战略物资,在冷战时期尤为重要,当时整个城市因为“镍”而形成,那里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建筑极为简易,人口结构比较复杂。刚好前两年我去过甘肃的金昌,这个地方与尼克尔的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只是规模更大一些,我和北欧的几个艺术家正在计划做一个“镍的项目”。
顾灵:这让我想到你开始关注地域性的东西,像这次展出的两件作品。之前做工厂的时候可能会把它看成现实环境相对割裂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现在可能特别关注工厂与城市,人的群体的关系。两个地图都涉及区域性的环境。你在拍摄这些画面以及最终的作品背后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文本及故事。之前在上海的展览还在讨论你作品中机械美学,工厂美学,到现在其实已经开始谈论你的作品中社会学的东西。无论是影像还是其他视觉的东西,其中已经牵涉可很多社会学调查的方式。

《区域》2 号 银片、铅片、清漆、铁粉,126×99.5cm,2017
李消非:流水线项目包含的内容比较广(不只是工厂的流水线),这几年它不断延伸,不断分支。我一直保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去一个工厂都把当时的拍摄经历、感受以及需要感谢的人等细节记录下来。到现在我慢慢的开始将这些感受和素材放在一起进行剪辑。
顾灵:拍摄了这么多个厂,你对制造这个概念有怎样的理解?
李消非:我可以说一组数字,像《崇明岛》中提及这个厂一个月生产一百万只锅,就是说一年最少做一千二百万只锅,这还不是国内的大厂。我大概算了一下,国内一年可以生产约一亿多只锅,全世界可以生产约两亿只锅。我一直在想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另外我们的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物质吗?走进厂里的一个抛光车间,里面温度非常高,强大的噪音污染和环境,那种感觉像炼狱一般。我在里面拍摄的时候,工人们根本不关心我在干什么,都在做自己的事情,那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在同一工作状态中与环境搏斗,到最后也都习以为常,希望都会在环境中泯灭。

崇明岛(视频截图)
顾灵:采访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像沙发厂的老板就说,中国的人口比例是葫芦形的,屌丝和最富有的人是最多的,小白(白领)和中产阶级是较少的,但是后者两个群体对中国健康的发展是重要的,所以你在这些工厂中会收集到不同的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李消非:对,我采访的老板层面的群体都过于聪明,感觉比我们的智商都高,该懂得都懂,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像你提到《沙发》作品中的那个老板,他不是从书上了解到这些东西,而是从长时间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很多知识分子从书本中得到的所谓知识,其实并不如在现场去了解、感觉这些人真实的想法。
顾灵:其实他们这些道理都懂,但他们还是为了赚钱为目的,该剥削的还是会剥削。
李消非:站在各自的立场,目标是完成不一样的。
顾灵:人是被妥协的,他的思路也不会有什么选择,尽管有能力去改变但还是延续一贯的做法。
李消非:是的,像崇明岛这个工厂已经是上市企业了,据说在业内排名第三,我想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往上看,如何尽快做到业内第一,至于下面的工人,我想他们无意做到感同身受。
顾灵:所以这些管理人员会把自己设定在一个范围里,他们考虑的是竞争,或者一些运营的策略。工人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工人就是用来剥削的。所以你之前说到的真实与虚幻可转换的边界,给我的感触就是在现场它是非常真实的存在。你在作品里面会考虑你的作品在多大程度里面反映了那个真实的现场吗?作为一个视觉作品它多少带有一种虚构属性的东西。
李消非:我作品的着重点不在这里,工厂是我作品的主要环境,我借用工厂的素材作为一个基底来进行外延,比如:景观性画面的植入,上海的周边的发展,以及水系作品“让水一直流”的项目……这些都是我想探讨的问题,这是流水线项目不断延伸的过程,我的作品不是在诉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非常的失败!

沙发(视频截图)
梁健华:陈侗老师在展览前言里也提到李消非在拍摄对象时其实一开始是有社会关怀的,我也了解到我们这一代艺术工作者身上多多少少都受这个现实关怀的影响。但我隔了很多年再看你的作品的时候,发现其实你作品的切入角度与我们理解中的社会性挺不一样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转到这种视角的。
李消非:我拍的画面其实不存在什么的艰难的感情。对工人而言,有工作是最幸福的事情。对我而言,能拍摄是最幸福的事情。你所说的这种现实关怀的转变,在我看来只是不一样的角度。在纽约的一次对谈中,曾有人问我,我是处于一种怎样的阶层。我感觉我的阶层是流动的不确定的,跟底层工人交谈的时候我也是工人;与老板交谈的时候我跟他是平等的;在画廊在美术馆与策展人、馆长工作时我是艺术家。
梁健华:所以你没太刻意讲究这个现实关怀?
李消非:是的,都是现场直接的反应。但工作多了以后自然会有这种现实的关怀。像我之前说的,我拍摄的关注点渐渐地从人的脸部移到工人的身体局部和姿势,这是最近的一个变化,不是事先设想好的。
顾灵:我觉得创作会影响人的认知,不只是方式上的,还有人怎么看这个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都会因为创作而改变。
李消非:曾经有人问流水线项目会不会流水线作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从成功学的角度我应该把它做成我的一个品牌,然后大量生产作品。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流水线项目自身应该有变化而且已经在不断的延伸。比如我会再次去以前拍摄过的工厂做回访,很多都和以前不一样了,社会在进程,老板的思维,工厂的状态、人员的结构等都在变化。
全荣花:想拍流水线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追求?流水线这个项目不是始于你对工厂环境的关注,而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流水线。我觉得你的视角与关注点很重要,像这次展览我特别希望你能展示出关于影像之外的另外的一些视角。
李消非:我想反映的是与工人意识有关的,这些都是容易被忽略的,企业不会去关注这些问题,工人本身也不关心这些问题,我只是通过艺术这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顾灵:我感觉这其实还是艺术家对事物的敏感度。我认为“艺术家想表达一个东西”这句话是被包装过的。艺术家去做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看到一样东西是“我作为我”无法忽视的,是这样一种被激活的敏感。
李消非:艺术还是有自己的系统,所谓的感受是最初的原状态,是一种被发现的逻辑思维,所以还是需要做大量的积累。
顾灵:像我之前说的创作的过程会改变人的认知,而不是我有的一些东西,我要把它表达出来就把它“掏”出来,在认识与发现的过程会改变自己的认知。

对谈现场
我们是否应该走慢点
陈侗:之前曾经有关于“抛弃当代艺术,向现代主义回归”这样的讨论。在现代主义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可以凭仗自身创造力进行创作。但在当代艺术里可能是在一个大集体中进行创作,比如说现在收藏家占艺术圈的70%,但在现实主义时期,艺术家可占艺术圈的一半。而我在消非的作品中看到一种现实主义的气息,如果我收藏消非的作品主要是因为这种现代主义的气息而不是当代艺术中的社会学倾向。我看到他的作品我想起一个关于“三反五反”时期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音乐教授有一天在饭堂,有个学生的盆子掉在地上摔碎了,教授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问学生能不能再打碎一个,最后音乐教授受到批判。我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的是教授对于音乐的热爱。我好奇的是消非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一种感觉,有时候艺术家创作的原动力其实与当代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作品在展出后会经过学术交流,会在当代艺术层面产生关系。但有时候作品停留在纯粹的一面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去发掘后面的社会性。回到美术学院的时期也没什么需要责难的,那时候的创作是很投入的。

陈侗:有时候作品停留在存粹的一面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去发掘后面的社会性。
李消非:陈老师是站在一个俯视的角度看问题,我在工厂拍摄的时候,艺不艺术,当不当代我都不太考虑,我只想用更好的设备将更多的细节拍摄下来,每次离开工厂我都觉得还遗漏些什么,所以有很多拍摄工厂,我还有可能再次进入。
徐坦:我是觉得现代主义的目的是建立主体。艺术家从看到什么,发现什么表现什么从而确定“我”是什么。但现在把这个主体放大了,像文学,音乐,现在很多关于主体建构的艺术的资源库被用光了。如关于荒诞的自我体验的描述,卡夫卡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创造当代交响乐的时候,艺术家还是要去听勋伯格这类音乐家的作品。这个主体是有限度的,所以关于自我的范围进行了扩张,你看世界就是看你自己。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看自我以外的社会和世界时,有可能缺少艺术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美学。现在社会介入被视为艺术了,但也有人认为社会介入不是艺术。这里面的意思不是不应该做社会介入,而是这些社会介入里面没有体现如卡夫卡和以前那些艺术家作品里面迷人的东西。这不是题材(体裁)的问题,而是美学的发现不足。如我们发现一个人在劳作,但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美学,不是说沿用了现代主义积累的经验,而是你没有新的美学去表达。所以就变成你说他还是他,而没有变成“我”。我估计这可能就是一些人不喜欢社会介入的问题,这里面的路还很长。引用中国的一句话“从‘看山不是山’变成‘看山还是山’”,说的就是你怎么把这个世界容纳到你的意识活动中去。消非的作品在拍摄机器的时候还是很有他个人的美学。
顾灵:不光是机器,还有更抽象的场景、人,创作里面的时间感,节奏,接近绘画的影像画面等视觉属性,还有他使用接近绘画的创作方法而非典型的影像创作方法。

流水线 No.14(视频截图) HD Video / PAL / Color / Sound / 3'11",尺寸可变,2015
陈侗:关于资源库枯竭的问题我之前也跟徐老师讨论过。我们是否需要走的慢一点?不要太快地走向终结。对工厂的关注可以有很多表达方式,画家绘画的表达方式的缺点在于绘画的节奏是不带声音的,它可以表达一个排列,图案中的联系,有序列的关系,但录像不同。从一开始,消非的动机应该与一个画家没什么两样,但采用录像比绘画的方式走前一点点,但不是太快。作为一个画家出身的艺术家是无法丢掉绘画的基础的。
徐坦:在90年代,我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是一个“进步主义者”,我那时候与陈老师有个讨论,说我要用西方最前沿的方式进行创作。他问我“然后呢”。我说接下来用更当代的方式。他又继续问“那再接下来呢?”我就回答不上来。他说“接下来人类就结束了”。现在我会想这次讨论我觉得陈老师当时的讨论很有前瞻性。一个人生长的速度越快,可能他到达终点的时间就越早。所以我意识到我们是否要回到东方哲学,天不灭道德不灭的时期。因为科技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惶恐。当我们回到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这种创作方式很boring(无聊)。如果我们要换一种视角看这个世界,那我们就要加速。当我们不断更换视角,这其实使我们进入到资本主义的规则里面。一个是行业的分离,导致加速改 变的竞争。如马云要开无人实体超市,有些富人在瑞士的山里做永生的试验……这些都是我们的穷人不想看到的。我觉得很被动的事情是我们的专业要求与专业的价值观都是与不断创造不断更换新的东西新的视角,但又担心远离东方哲学。

徐坦:关键问题是:哪个系统是对未来有意义的系统呢?
陈侗:时间对艺术有一种作用。多少年以后,现在的作品看上去已经过时了,但以前的一些作品还不过时。它们的区别在哪呢。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品如果是受什么东西的影响,是去模仿、概括一个认知的过程,它就有可能会过时,如85时期的一些作品现在看来放在当时都是过时的,这里问题就很大了。但如果一个作品与认知过程没有关系时,是生长出来的,哪怕它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要求,放在这个时代也不会过时。我们一方面要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方面走的慢一点。正如长寿跟健康是两个概念嘛。
徐坦:我要反驳陈老师的观点。我认为任何过不过时的认知是系统造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作品在未来是不过时的。我有一次在旧金山moma,看到一个导览在一群老头老太太面前对着小便池作介绍。老头们很疑惑地看着这个作品。他们肯定在书上看过这个作品,但这个作品是否与他们家中的小便池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如果跟认知无关的话,它有什么美学呢。所以所有的这种评判都是系统造成的。比如我觉得这个作品不好,但系统告诉你“你必须欣赏他”。关键问题是:哪个系统是对未来有意义的系统呢。
顾灵: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预测认知系统本身会怎么改变的能力。

未知域(展览现场) 铁粉、油漆、金属配件和零件,120×120×25cm(3pcs),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