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DawanArt

威廉·阿道夫·布格罗《被复仇女神追逐的俄瑞斯忒斯》115 × 185 cm 1862
【大碗按】八十年代的法国见证了艺术市场的空前盛况,与此同时,法国文化部对艺术的大力投入与扶持、消费群体与公众的热情都极大地推动了当代艺术的发展,然而一夜之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市场迅速瓦解,各种期许一一落空,刚走红的艺术明星忽成昨日黄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关于当代艺术的大讨论席卷了法国文化界。
1991年,左派人文期刊《精神》(Esprit)发表了让—菲利普·道迈克(Jean-Philippe Domecq)揭露当代艺术之“骗局”的文章,引发了各媒体的大讨论,不同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人士都参与进来。让·鲍德里亚在《解放报》发文批判当今艺术创作的“无价值”。1996年底,《克里西斯》(Krisis,希腊语“判断”之意)杂志专号《艺术/非艺术?》(Art/Non-Art?)将争论推向高潮。鲍德里亚、道迈克和当时的毕加索美术馆馆长让·克莱尔(Jean Clair)是这期杂志的主力,他们对当代艺术的责难,尤其是在《克里西斯》这份右派杂志发表文章的事实,引发了左派评论家阵营的极度反感。卡特琳娜·米莱(Catherine Millet)以自己主编的Art Press杂志为阵地组织回击,推出了抵制“极右派攻击当代艺术”的专刊。1997年,《费加罗报》再度出击,法兰西院士马克·弗马洛利(Marc Fumaroli)和让·克莱尔大谈“当今艺术的死胡同”。对此,《世界报》专栏作者菲利普·达根作出激烈回应,称这些人为“审查官权威”,他们正进行一场“反动游戏”。这场论争也被戏称为二十世纪末的“古今之争”*,它所折射的不仅是当代艺术的危机,也是整个西方文化所面临的悖论和困境。

1997年,作为这场论争的成果,两部大作问世,一是“保守派”代表让·克莱尔的《艺术家的责任》(La Responsabilité del’artiste, Ed. Gallimard),该书前两年已译成中文出版(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另一部是“创新派”代表菲利普·达根(Philippe Dagen)的《对艺术的仇恨》(La Haine de l’art, Ed.Grasset)。在《对艺术的仇恨》中,达根指出法国公众与当代艺术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法国公众仍在迷恋印象派及其先驱和后继者,如果说公众对艺术展览趋之若鹜,那只是对于类似雷诺阿、高更和梵高的回顾展的趋之若鹜,而当代艺术则几乎没什么观众。国家对当代艺术的投入近乎“施舍”,当代艺术的赞助人和收藏家在法国也寥寥无几。达根认为,法国人对当代艺术简直怀着某种“仇恨”,他们过于怀旧,从未真正接受一个乡土的、田园牧歌的法国向现代的、工业化的法国的过渡。他们拒绝二十世纪艺术的革新,他们不喜欢立体主义所代表的战争和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断裂,他们也不喜欢波普艺术和沃霍尔,他们同样回避最新的艺术创造对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变形处理。
因为菲利普·达根《对艺术的仇恨》一书还未翻译成中文,使得这场争论在汉语语境中略显偏颇。大碗艺术本期与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序言,为的是让大家对这场争论大约有一个整体上的认识。当类似的争论投射到现今中国艺术界时,大家不至于因为对争论的背景无所知而产生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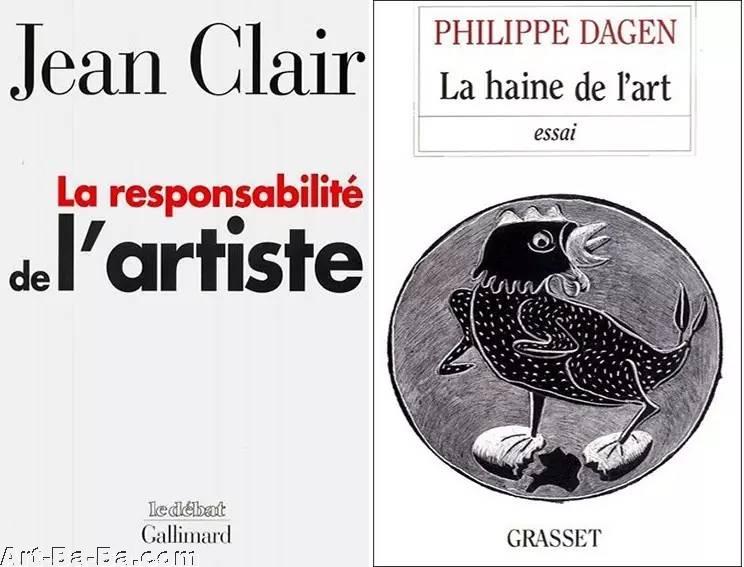
《艺术家的责任》和《对艺术的仇恨》的书封
菲利普·达根《对艺术的仇恨》的序言
翻译:小木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很天真。这是一个幻灭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很冒失,这是一个苦涩的故事。
我们,只是很少的一些人。早就应该当心。我们,是一小撮找茬的人。早就应该有点远见。
我们,是被归入“当代艺术圈”的人:艺术家、批评家、美术馆人员、爱好者。一个“小圈子”,人们经常不无讽刺地说。
曾经有过一些最怪诞的展览,曾有过一些来来往往的外国艺术家,曾有过讨论、争吵、冲突,有过动摇现有美学体系的快乐,任由艺术作品自行其道的快乐。曾有过一种好奇心,它拒绝承认满足,渴望着不同形式的渎神和断裂。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曾有过这一切。参与者和见证者都还在,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历史会给这一时期冠名;或许某个艺术家会渐渐成为标志,他的作品将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我们时代的象征。
曾经有过这一切,但今天,这些事件和对话似乎只可能被当作某些流亡者和隔绝者的现实与姿态,他们从内部逃离出来,并不比薄伽丘《十日谈》中的讲述者们处境更好,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花园里,而外面则瘟疫肆虐,吞噬生命。
并不缺乏预言性的征兆,显示人们疏于阐释,且没有足够悲观的预期。很长时间以来,哪怕最不敏感的人都已经注意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艺术家们只拥有很少的观众。他们知道画廊和美术馆为今天的艺术家举办的展览无法吸引太多公众。他们知道蓬皮杜中心的成功主要在于它奇特的建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去看现代主义以后的藏品展,多数人是去参观自动扶梯和城市景观的。

他们知道,这种多数人的冷漠,在巴黎已很明显,在外省更为严重。他们知道各种艺术中心主要的观众是学校组织的学生。他们知道,很多作品只会招来嘲讽和愤怒,公众们或沉默或抵制。基本原则是:不要触动历史的纪念碑,不要让人们感到为难,要尊重过去。人们甚至曾以保护动物的名义签署过一个请愿书,反对一个艺术家将一群昆虫关在玻璃盒子里让它们自相残杀。这些对抗不会消失。但还是应该抱以希望,希望公众逐渐习惯和接纳当代艺术。
无论习惯或接纳都不会产生显著的效果。对抗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加强。有一天,人们会宣称,这种当代艺术既无意义也无趣味。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成为一种恰当而流行的说法。这种艺术,连同它的欺骗、诱惑和荒唐,都该结束了。真正的生活在别处,真正的艺术也同样。
一开始,这只是一些怨恨的论断,无关紧要。一些来路不明的作家,或是披着哲学的外衣,或是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号,表达了他们的厌恶情绪,这种厌恶是他们在美术馆、艺博会、画廊里看到的东西所引发的。他们激烈地道出了对法国当今艺术的蔑视。读一读他们在《精神》杂志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当代艺术的了解是非常模糊的。显然,愤怒没有留给他们太多的时间去观看他们所诋毁的事物——他们混淆了一般的美国艺术家和作为个人的沃霍尔,混淆了先锋派和作为个人的杜尚。毕加索,无疑是二十世纪艺术和文化的试金石。他们发现,在法国存在一种官方艺术,由文化部的官员们发放津贴,他们认定这种畸形的模式是从上个世纪延续下来的并对此大加谴责。这些发生在1992年,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四年后,第二场论战开始了。作者不再是同一群人,他们的声望、企图、方式和论据也全然不同了。人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些想以挑起论争而出名的初出茅庐者,三位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先后登场:鲍德里亚、让·克莱尔、马克·弗马洛利。第一位揭露了“艺术的阴谋”,另两位以对话整理稿的形式发表了他们类似的观点。鲍德里亚和让·克莱尔还在《克里西斯》著名的《艺术/非—艺术?》专号上发表了文章。在一份新闻周刊上,让·克莱尔继续出击,宣布“法国当代艺术不再有意义也不再存在”。其他周刊纷纷回应——所有这些都超出了传统政治倾向的考量,难以划分右派和左派,文章也分散在不同立场的报刊上:《解放报》、《费加罗报》、《周四新闻周刊》、《玛丽安娜》等等。论战事件没有很快平息,却变得越来越严重和复杂。
这次,由于参与者的声望和他们的观点不容置疑的强力,几年前《精神》杂志对当代艺术发出的最早的诅咒终于汇聚成巨大的声音:一场辩驳和反辩驳的战争。恶意中伤、据理力争、电视辩论、公众讨论,一样都不缺,最重要的还包括国立巴黎美院的大讨论。这些搬上舞台的争吵,使观看者好像置身于一场拳击盛会,只可惜太多的攻击辱骂并未产生真正的智识上的收获。
似乎突然间,当代艺术引起了严重的不理解和厌恶,无论发动论战者还是观战者都没有预料到这种不理解和厌恶的威力。他们没有预料到这种怨恨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他们应该明白这一点,虽然长久以来,他们都佯装不知。因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出于信任而资助当代艺术,还有一些专门的非营利美术馆和刊物。当这种信任被指责为轻信和盲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那些宣称今天的艺术无价值的人,在有一点上至少是明智的:公众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所说的东西顺应民意。他们中的一位最激进者曾经写道:“我们不能永远进行自我审查。”
这不是第一次了。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并非仅仅传达审美效用,他们有着其他的动机、缘由、准则和传承,所有这些话都不是第一次说了。对他们的仇恨也不新鲜,批评的主题和标准更不新鲜。自十九世纪以来,这简直就是法国文化艺术生活的传统话题,就像政治生活的传统话题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纷争被隐藏在沉默寡言的氛围中,一旦被激起,立即成为雄辩和炫耀,为了哗众取宠,赢得众意。
这本书并不是要详细讲述一场论战,这场论战最终成为个人间的争斗,能力与权力的争斗。也不是要为被称为“当代艺术”的偶像谱写一曲赞歌。艺术家们仍在不断地掉入风格、重复和学院主义的陷阱:在我们的当代人中,很大一部分都在迎合自以为创新的俗套。各种机构的缓慢和僵化加速了这种变质。
所有这些思考都不足以终结这些事件。对当代艺术持续的激烈的仇恨,会唤起其他的分析研究,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美学的。一种法国式的意识形态加剧了这种仇恨。对文化遗产的崇拜支持这种仇恨,文化消费也遵从传统的权威。国家对这种情况的回应十分无力,当代艺术的爱好者们也没有显示更强大的活力。知识分子只要自己不做这方面的理论,对所有这些现象都很宽容。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一点点地仔细观察、描述和衡量。这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研究事物最新的发展以及它曾经的表现,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理解它并为它战斗。▧
*古今之争,17世纪末叶法国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崇古与崇今的争论,史称“古今之争”。一边是以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Fontenelle)为代表的厚今薄古派;布瓦洛(Nicolas Boileau)、拉辛、拉封丹、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等人则站在古人一边,主张人类是在不断堕落的,古人在政治哲学、文学上的成就为现代人所不可企及。两派文人学者意见冲突,反复争辩,相持不下,争论一直持续到18世纪,甚至蔓延至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