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瑞象馆 btr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一生都在写同一本书。从1968年的处女作《星形广场》到2014年的小说《这样你就不会迷路》,他一次次深入记忆的迷雾,追寻二战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他的小说“运用回忆的艺术,唤起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揭示德占期间的人间世象”。(诺奖颁奖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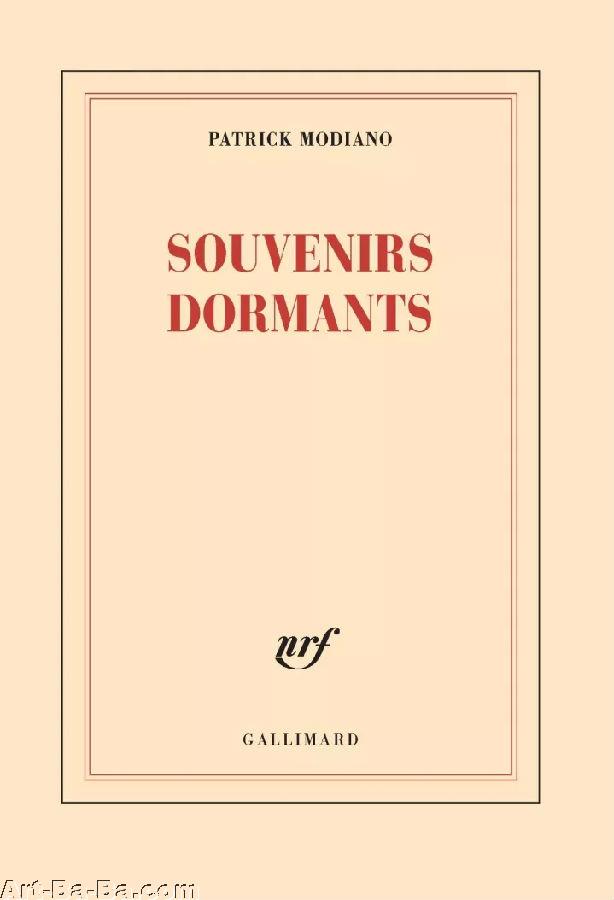
《沉睡的记忆》
就在上周(10月26日),伽利玛出版了莫迪亚诺后诺奖时代的首部作品《沉睡的记忆》(Souvenirs dormants)。可以把新书页面上的摘要视为对莫迪亚诺小说的精辟总结:“对此你有一些记忆……是啊,有很多……但我也记得一些生活细节,记得那些我试图忘记的人,我以为可以成功忘记他们,但不曾料想多年之后,他们又浮上表面,像溺水者,在一天里的某个时候,出现在街角。[1]”
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新中译本《狗样的春天》(Chien de Printemps)里,莫迪亚诺借叙事者(一位作家)之口,道出了他的记忆显影术与摄影之间的关联:“应该相信,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
绘画与摄影
在莫迪亚诺看来,十九世纪的社会是稳定的;普鲁斯特所追寻的逝去的时光如同一幅生动的绘画。然而,对于德占时期的巴黎——即1945年出生的莫迪亚诺的童年时期——记忆则是不确定的。那些记忆被遗忘的巨大白页所遮蔽,如漂移的冰山或弥漫的雾气。“我们只能捕捉到往事的残片、中断的线索、逐渐消失且几乎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2]”因此,如今小说家的工作是“如同红外线和紫外线一般发现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东西。”
一如绘画之于十九世纪的小说,照片成为莫迪亚诺小说最恰当的转喻。“小说之于读者,类同于照片的显像,我指的是数码时代之前的做法。暗房里面冲洗的照片是慢慢显现出来的。当我们在小说的阅读中前行,同样的化学机制也在发生。”而阅读与写作过程是这一显影的正反两面。
《狗样的春天》是参破莫迪亚诺记忆显影术的最佳入口。这不仅因为小说写于1993年,莫迪亚诺文学创作最成熟的阶段之一,在有限的篇幅(约四万字)里展现了其一以贯之的娴熟的叙事技巧;而且因为小说的两位主人公恰好是作家与摄影师,“显影”过程同时发生在小说的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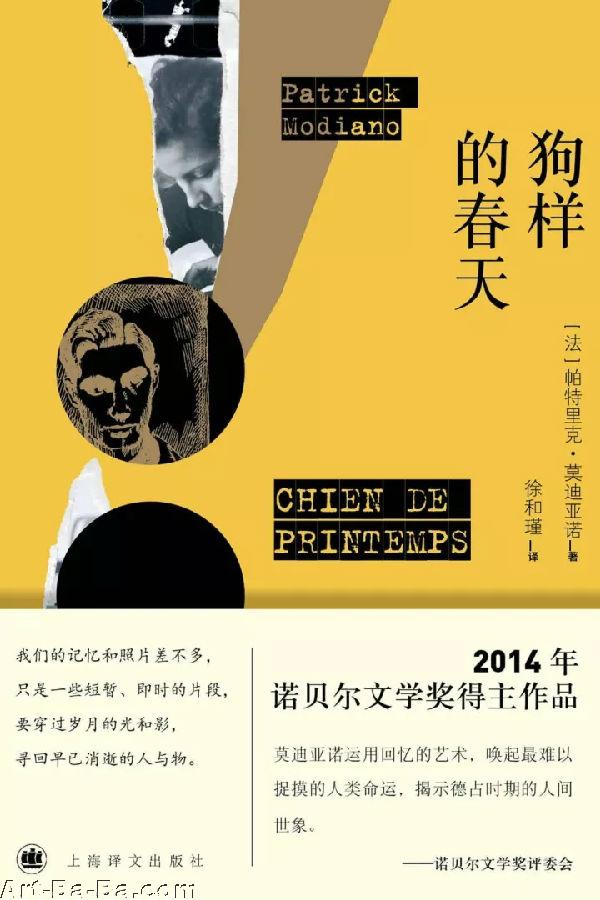
《狗样的春天》
小说里的作家与莫迪亚诺一样生于1945年,具有浓烈的自传性色彩;而比他年长34岁的摄影师冉森,则是一个典型的父辈角色。他1938年来到巴黎,为好几位摄影师当助手,随后结识了罗伯特·卡帕,并一同前往西班牙拍摄西班牙内战;德占期间,他一度被捕,又被领事解救;战争结束后,他开始为玛格南图片社工作。1964年6月,他带着三个手提箱的照片突然离开巴黎,有人说他去了墨西哥。
熟悉罗伯特·卡帕的读者一定看出了端倪:冉森这个虚构人物不啻罗伯特·卡帕的化身(或分身),而那三个手提箱也确有其事——1939年后被认为已遗失的有4500多张35mm负片的“墨西哥手提箱”[3]于2007年末重现于世,其中包括罗伯特·卡帕、彼时女友格尔达·塔罗及大卫·西摩所拍摄的大量西班牙内战照片——不过,莫迪亚诺要写的并不是一本关于罗伯特·卡帕的传记小说,他也并不囿于史实,而是借用摄影师这个人物深入尘封的往事,对摄影和照片的本质及其与写作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思考。

墨西哥手提箱
寻找“自然光”
摄影同时作为内容及叙事手法的隐喻贯穿于《狗样的春天》之中。全书围绕叙事者(作家)对冉森谜样往事的追寻展开,尘封近三十年“处于冬眠状态”的回忆之所以突然重现,恰是因为一张照片——三十年前冉森所拍摄的叙事者与女友的照片,“反面盖有蓝色字幕图章:冉森所拍,禁止翻印。”
两个春天如重复曝光般叠印,叙事者回忆起他们相遇的那个早晨。在巴黎的露天咖啡座,冉森迅速而又漫不经心地将镜头对准叙事者和女友,当时的他已厌倦了为美国杂志拍摄商业照片,“不想再做这种有报酬的工作。”然而更意味深长的,是莫迪亚诺描述叙事者三十年后重看旧照时的感受:“我感到这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两人,这是因为时光已经流逝,或是因为冉森在镜头里看到的形象,我们当时即使站在一面镜子前也无法看到:那是两个迷失在巴黎的无名少年。”
从身份确凿的“我”和女友,到“两个迷失在巴黎的无名少年”,莫迪亚诺借由旧照片这一媒介将个体的命运延展到了群体。在莫迪亚诺的小说里,德占期间的人之命运常常具有双重性:每一个幸存者都不断提醒人们有其他人未能幸存。在小说结尾,当发现同名同姓的另一个冉森在集中营里死去时,莫迪亚诺写道,“一个弟弟,一个化身替我们死去,死在一个不详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幽灵最终跟我们混杂在一起。”[4]
除了“照片-化身”的隐喻外,可以将小说里的“我”为冉森整理手提箱照片的过程与三十年后的叙事者试图“整理”往事的片段作一番类比。叙事者当年提议为冉森整理照片,是因为觉得“这些照片有资料价值,因为它们是消失的人和物的证明”——呼应了罗兰·巴特在《明室》中的“此曾在”(ça-a-été)理论,然而冉森却宁愿选择遗忘,尽管拍摄时他曾在照片背面注明人名和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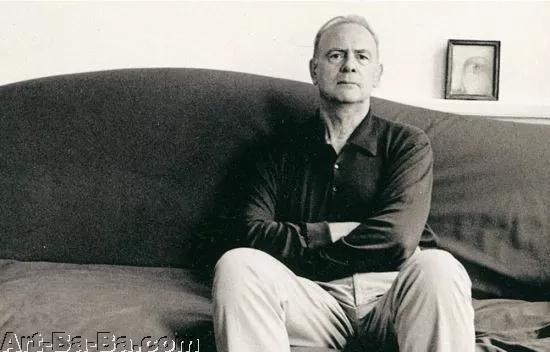
莫迪亚诺
与德国作家泽巴尔德(W.G.Sebald)将图像直接插入叙事中的处理方式不同,莫迪亚诺用文字描述照片,凸显出这些文字在读者的想象中所激发的画面的不确定性。而其碎片般的、不被解释的特性与记忆的特性暗合。MoMA策展人John Szarkowski曾在1964年的展览《摄影师之眼》[5]中这样分析(战争)摄影:“摄影师在工作室之外无法建构真实(pose the truth):他只能按原样记录,而本质上它是破碎的、未经解释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分散的、暗示性的线索。摄影师无法将这些线索组装成连贯的叙事,他只能孤立片段,记录它,并通过这样做赋予它特别的价值(……)如果照片无法被当作故事阅读,它们可以被当作象征(symbols)。”而战争摄影放大了摄影中“叙事的贫困”及其象征力量。由此,摄影、记忆和莫迪亚诺的叙事策略统一了起来。
在《狗样的春天》里,莫迪亚诺的这种记忆显影术由冉森所推崇的“自然光”概念抵达了另一层隐喻。所谓“自然光”,是指战争期间美国新闻摄影师所使用的泛光灯,它是一种可以向四面八方均匀照射的电光源。换而言之,“自然光”之“自然”是需要通过人工的方式达成的,这与通过虚构的小说抵达某种更本质的真实如出一辙:人物、故事、背景都是虚构的,然而它所揭示的、显影的、令读者逐渐浸润其中的东西,却是真的。
注释
[1]见:https://www.amazon.fr/Souvenirs-dormants-Modiano-Patrick/dp/2072746310/ref=asap_bc?ie=UTF8
[2]见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4/presentation-speech.html
[3]见https://www.icp.org/exhibitions/the-mexican-suitcase-traveling-exhibition
[4]分别见《狗样的春天》P3和P94(徐和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
[5]见《The Photographer's Eye》(The Museum of Modern Art,2007年重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