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征空间

展望对话曾焱:在行动中不断反思形与体





图片由YT新媒体&长征空间共同所有
问:2018年意味着00后的一代开始成年了,算是一道分水岭。你们能谈谈18岁时的情境吗?
展:我16岁上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之前绘画是兴趣,上了美校后,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同时还拼命看书。18岁,我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印象深刻。这套书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启蒙了我看待问题时的批判眼光。读这本书前,我对文艺复兴是完全膜拜和学习的心态。而本书中的两位主角则是以批评的态度对待文艺复兴以来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文化,不是仰视,而是以平视的态度,评论、判断地发表观点。
曾:18岁,我进入大学,这个阶段完全截断了过去的中学时光,也是第一次对自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那时候我还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那个阶段的人生主题也变成,如何在一个集体的状态里面去找到一个自我最好的状态、明确自己的位置。大学期间我选读新闻系,就是要做一名记者。新闻系在当时是特别时髦的一个专业,大家都有“铁肩担道义”的理想。我甚至会觉得,一支笔可以做很多事情,迄今为止我还在做,所以我认为我算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比起当时,理想可能更完善了一些。

展望,《坐着的女孩》,1990
展:18岁的时候,我对我的未来没有清晰的规划,但是有一点确认的,就是我这辈子肯定要做艺术。我觉得文科生和艺术生不一样,艺术生总想要做些带有破坏性的事情,不断地寻找潜在的突破点,寻找自我,愉悦自己。
曾:是的,确实有差别。比如说新闻这行一定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真的就是要承担一定的社会道义。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对于自己边界产生好奇,即我能突破到什么程度。
展: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边界”这个词,并没这个概念,只是想出新花样、恶作剧、玩点好玩的事。当别人都循规蹈矩的时候,我就想别出心裁做事。不锈钢假山石的诞生就是这样,当整个艺术潮流都是做旧,或者做现成品,我就想亮一下、俗一下;又比如我在九十年代做的清洗废墟行为,也是当时未曾有人做过的。

展望,《空灵·空 - 葬中山装》,1994 -2003
曾:您能讲讲九十年代初,你在做清洗废墟时的艺术创作环境吗?因为据我所知当时是没有所谓的艺术商业或者是任何展厅可以承载您这些作品的。
展:那是1994年的时候,当时之所以这样做,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学校,以及学校所处的王府井文化街区,竟然要被拆掉盖商业大楼。当时也是新媒体、观念艺术和装置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当时想,雕塑能不能在户外做,在公共场所的创作是否更有利于深入到社会?而整个大环境,北京要从一个中世纪的城市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城市,我就想如何介入这样的社会事件。当时我们有一帮人一起玩,朱昱,余凡,大家爱找事干,这也是一个理由。总之各种缘由促成了这一个行动的契机。我当时想的方案就是在拆了一半的废墟进行清洗、装修,比如脏的地儿擦干净,然后重新粉刷。现实中,我非常反对拆王府井,它是民国时代的那种中西结合的建筑,有花园、假山石,这么好的建筑给拆了,很可惜。当你把这个废墟看成是一个雕塑,里边有擦洗的、粉刷的动作,涂色和绘画,于是各种与美术相关的动作都能融进去。后来有一个批评家写文章说我在为死人化妆,这个形容很像,因为这个废墟就相当于将死或说是一个死了的人。

展望,《第八十六尊圣像》,2008
曾:一般大家都希望能在你早期作品和目前创作之间寻找一条线索,你觉得之前的这些东西跟你后来做的雕塑,它们在你的创作上留下了什么印记?
展: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在1994年做的这种清洗行为,给我的启发就是,用行为来表现自己的想法,这个理念很快融到了第二年(1995年)我开始做的假山石上。因为假山石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不锈钢的闪亮的东西,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它的制作过程。制作假山石就是一个行动,先找块石头,然后用钢板覆在上面去拓制。在古代拓是学习的行动,拓石头不就是学习石头吗?那学习石头代表什么?代表自然。那么拓石头等于向自然学习,也就是说拓本身这个行动就在传达意义和思想。之后无论是镶长城还是公海浮石,这些艺术语言都是因为它跟行动有关,而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制作。比如说“新艺术速成车间”就是一个雕塑的行为,把雕塑过程变成表达方式了,还有“埋葬中山装”、“我的宇宙”,甚至到最新的用火烤的“隐形”都伴着行为的因素,所以行为对我来说不是行为艺术,而是行为雕塑。
曾:所以大家会称你是观念雕塑?你认可这个定义吗?
展:其实这个定义是我先说出来的,但它很容易被人误解。因为人们马上会想到观念绘画、观念摄影,但是它们的不同在于,雕塑的动作特别重要。
曾:我上次去听你给学生讲课,你给学生开了一个行为课,对吗?
展:是的,我创作课的第一节是行为课,第二节是材料,因为我就是让他们开始从行为上认识材料,然后再进入材料。

展望,《假山石 No.59》于大英博物馆,2005
曾:这个顺序应该也可以说是你的艺术创作的一个出发点。其实好多人对你龙美术馆展览第一观感是作品的庞大。但我觉得在你从假山石到后来的悬挂的作品“隐形”,我感受到的有一个关键词“体”。比如最开始假山石也是一个体,然后到你的新作,把自己的扫描体丢在计算机里面,实际上你把自己对体的认知、感受和它的拓展都放在你的作品里体现。我觉得体其实是一个很哲学的感觉,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具象的东西。
展:首先你说的“体”跟我用的“形”是有重合的意思。但是你的“体”内涵很大,带有本体的意思,如果我们把它用学院的词来形容。就是造型,无论你所说的体、我的形,其实它的根本是造型。为什么我要把造型这个事又翻出来,其实是有原因的。整个九十年代我是反对造型的,我接受的是后现代的思潮,又从事当代艺术的创作,当代艺术反对的对象就是造型。过了十几年,我发现在反体、反形的时候实际上追求的是意义社会化,变得只有观念,只有哲学了。我认为这条路是一条死胡同,但艺术还要走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回头,回头绝不是复古,不是回到过去的造型,而是在我们经历了观念化的基础上,再来看什么是造型。这个时候我会有不同的体会,造型表述了世界本身的形状,代表了它的内涵。我们把它捡回来,重新观察,你会发现一个新的道路。
曾:这个展览,我的感觉是确实能看到你整个人思考的过程。

展望,《打开 1#》,2012
展:比如说1998年的《新艺术速成车间》,它也是对造型的反思。比如说《心形》,心脏的跳动产生了不同的形状,形的背后是体,也是本质。即便是我们赋予事或物一个意义,它仍需要附着在形的上面,如果我们只活在意义和观念当中,形的历史就结束了,那么艺术也结束了。为了不让艺术的历史结束,我要重新挖掘形的可能性。我后来一系列作品叫“应形”、“幻形”、“隐形”,其实它们各自都有出处。比如说“应形”来自于应物象形,应物象形是造型的一个中国式表达,但它是有局限的,必须先有物。但是应形不一样,只要跟着形思考即可成形;幻形,世界上没有形的实体就是幻想出来的形;隐形,就是潜在的、看不见的,经过思考表达出来的不同的形。“隐形”创作源于我儿时掉入岩浆的幻想,后来在太湖石不锈钢表面,一刹那间观察到无限的反射,于是我思考如何把一个瞬间的东西形成一件作品?于是我借助科学,在虚拟的计算机当中模拟了这一切。
曾:从前科学跟艺术的关系其实是没有给人带来太多的压迫感,但是好像到了人工智能的这个阶段以后,尤其是棋手输了阿法狗以后大家就很有一种担忧,就是艺术会不会也被人工智能所摧毁或者是取代吧,你有没有这种忧虑?
展:我没有,我一直觉得艺术家思考的问题是具有原发性的,无法取代。

展望,《隐形 1#》,2017
曾:你看其他雕塑家做的作品,有没有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使用新技术的一些作品?
展:有。比如说杰夫·昆斯的玩具狗,以不锈钢镀色,颜色高级而漂亮;我这次隐形做完了以后一开始我也想给它上色,但是上完色以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花了半年的时间,后来我进行实验,我才把上色这事给突破了。我的上色纯粹是烧出来的,它不光跟岩浆的这种灼热有关,它跟人的心理、内在的这种痛、瘾是相关的。
曾:你还是比较看重那种创作过程中原生的东西?
展:对,就是图像、材料、行动它本身含着那个意义,而不是解释出来的,对于观众来讲是感知到的,而不是听到的。
曾:哈罗德·布鲁姆的 “影响的焦虑”,提到自我能不能超越和自己做同样事情的人或者是前辈。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更切实的挑战是我能不能超越我自己以往的作品,或者别人对我的已有看法。你在做龙美术馆这样大型展览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影响的焦虑”的状态?
展:肯定是有的,从我答应这个展览到这个展览开幕,全都处在焦虑当中。因为我的目的就是从概念上、视觉上都超越之前的作品,所以感觉特别难。隐形的制作过程也十分艰难,离展览开幕不到一个月,还是没有达到我满意的上色效果,最后一刻我突然领悟,上色一定要跟行动相关,那就是”火烤“。

展望,《小宇宙 5#》局部,2017
曾:你在创作假山石之后,有哪一个阶段曾经遭受到的艺术批评是最猛烈的?
展:“假山石”后期受到的批评就很猛烈,说我的作品过于的套路化。有些批评是对的,确实在一定的时期里,不可能每天都创作出划时代的创作。你也聊聊你的生活、工作吧?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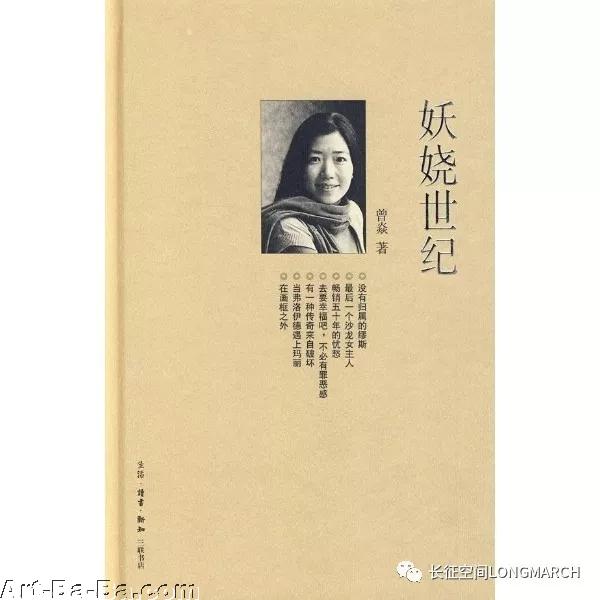
曾焱,《妖娆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曾: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已经工作十几年,虽然不能和艺术家的创造力相比,但实际上我们也在某一个阶段不断地思考如何突破自己。因为我们的工作本身会不断地重复自己。比如说做艺术报道,我采访了这么多位艺术家,如何才能在每一篇艺术报道里面让读者看到不同的东西?如何做到不重复同样的写作方式,或者不让每一则故事看起来都像从同样的模具里出来,挑战也很大。因为采访写作一个非虚构的东西,特别受制于对象与事件本身。即我不能有太多自己的观念,也不能被别人的观念左右,尤其是我们杂志会非常强调中性地观看。这样的写作,实际上就是给你划了一个圈,你在这里面跳舞。
展:你们完全反对主观性吗?
曾:不完全,但是特别强调不能过于主观去呈现事件或者人物。三联因为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怎么在客观的基础上又同时有自己个性的写作,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和挑战。
展:那如果客观,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客观的背后其实是发现。
曾:对。你现在回头来看艺术和艺术家的时候,你觉得艺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还会考虑这个问题吗?
展:会考虑。我们简单的来说,艺术可以无意义,如果说人类社会所有的工作都有用,那么艺术是唯一无用的职业。按照老庄哲学这种道家观念来讲,有用都是相对的,即艺术是没用的,但实际上它有用。这个有用体现在哪儿?是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人类社会当中有用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规训了,总得有人有自由的想法吧?那么最有可能就是艺术家。艺术家的自由是绝对的,所以我觉得把艺术放在这种辩证关系里来看还比较有意思,不能把它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