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装男士 文:海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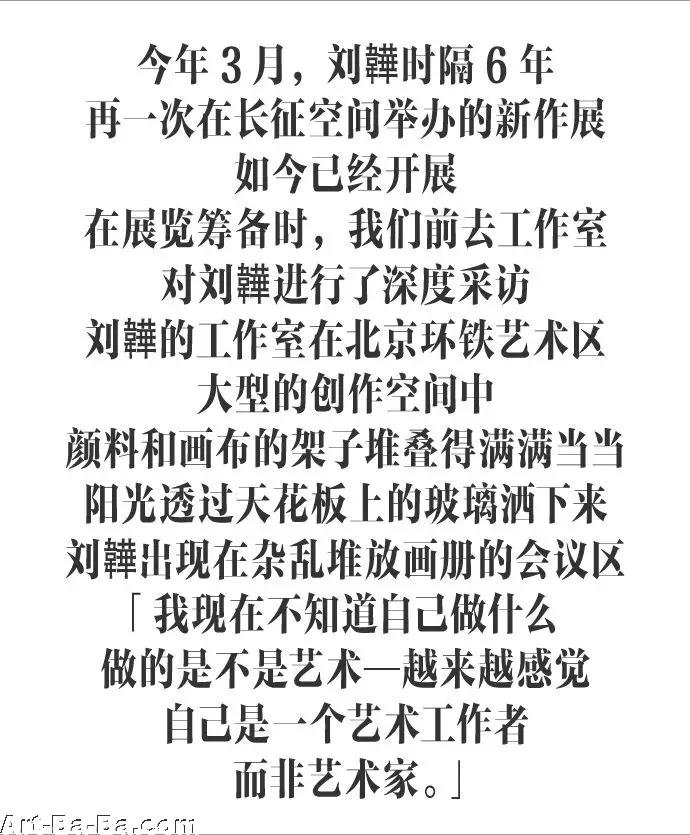
「简单直接」与「充分自由」
1972 年出生于北京的刘韡 1988 年考入浙江美院附中,1992 年考入浙江美院油画系,“每天就是踢球,一帮人也不知道做了什么,整天晃来晃去,喝酒、聊天……”晃荡到毕业,刘韡回到北京,在北京青年报担任美术编辑,与邱志杰、徐震、杨福东等人发起“后感性”运动,从那时起,他就将自我感受作为创作起点。他的早期创作《难以抑制》以多通道影像装置展示了如蚂蚁一般乱窜的裸身人体反复在地上爬行和扭打的景象。

人过而立,2004 年,刘韡辞了职,全身心投入艺术,“那时候艺术系统有了变化,有了当代艺术的概念,有了市场,开始有了一切。”刘韡回顾。2007 年,刘韡展出了令他声名鹊起的《徘徊者》,他利用从废品收购站搜集来的旧门窗、家具、桌椅等搭建了一个“封闭”的、“透明”的巨型建筑空间;透过玻璃窗户,观者可以目睹和间歇性地体验内部被风扇粗暴吹起而弥漫于整个空间的灰尘。在评论家鲁明军看来,观者可以接近甚至碰触作品,又无法进入装置内部,刘韡
无意制造一个观者可以随意介入的剧场,而是将其从观看的主体转化成一个被动的角色。他的《迷局》由镜面制作的形体构成了一些类似中国古代园林的结构,错落有致,但其间的局部又夹杂着刘韡切割物体的某些线条,使之具有陌生感—在刘韡看来,镜面的光象征着“光阴”与“命运”。与《迷局》互为照应的可以说是《受难》这件以铁皮为主要创作材料的作品:层叠或单片的银色铁皮,四周由黑色铁框围住;银色铁皮被切割、折叠,整体创造了一个来自虚空的开放性状态。而广受评论界喜爱的《爱它,咬它》系列,使用狗咬胶营造出摇摇欲坠的大型建筑结构,“事实上,我并不在意这些狗咬胶装置的具体形状,我关注的是某一种感觉,或者是这些作品的某种肌理”,刘韡说。

▲刘韡,《迷局ε》,2014,玻璃、铝合金,301 x 355 x 348cm
六年前,刘韡在长征空间举办的个展明确地表明对作品及展览的“拒绝描述”,没有名字、没有材质、没有尺寸,前台有一张简介明确写着“刘韡拒绝描述这个展览和作品”—他觉得那些堆满文献的展览方式“太古典、性感,而且污浊”。因而《迷中迷》尤为特别,刘韡还是忍不住透露了创作动机:“这件作品与平等有关,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盖过其他的部分。在这个装置中,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必须是平等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过分突出。”观众可以进入《迷中迷》由绿色帆布和大块海绵搭建的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材料的色彩和质感营造出丛林探险的气氛,而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又很难不令人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式厂房。“帆布在我很多作品里代表着丛林和适者生存”,刘韡说;这件就像由工业化的丛林构筑的时代迷宫一般的作品上烙印的国营生产单位字样,被策展人、评论家皮力目为“直观唤起人们关于集体经济生产时代的记忆”。

▲刘韡,《谜中谜》,2014,综合材料装置,尺寸可变,展览现场图,Blaise Adilon摄,里昂双年展,2015
刘韡的诸多作品,都有奇怪的形状—坚固的几何形体、繁复的构造、高耸的尖顶,让人仰望,也似乎能迫近地构成伤害;而那些作品的纯色,既是现实世界的表象,也是一个内在世界的逻辑,既是一种区隔,同时也在遮蔽区隔,既在建构秩序,却又试图摧毁秩序。“我是一个视觉艺术家,我的表达是视觉,颜色是我们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它覆盖于概念与材料之上,构成了我们区分事物、态度、阶级、好恶以及一切的万物。”鲁明军认为,刘韡的实践凭靠的是一种直觉和判断,有时作品简单到极致,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几何体,也有可能是几个色块,亦或是几块镜面;而有时,作品又繁复到极致,一张画要几个助手花费几个月实践完成,一部装置兴许囊括了数十个复杂的建造结构,“但无论简约,还是繁复,它们都显得极具锐度和重量。”对于刘韡来说,艺术不外乎两个问题—在表达方式上,要“简单直接”,在创作形式上,要“充分自由”。
一件作品在哪一刻停止
一言以蔽之,真的很难用语言准确地描述刘韡的艺术实践,“刘韡更多地是通过完全视觉艺术的方式来反对艺术的观念化。他所有的观念都围绕着视觉来进行—他用很‘视觉’的方式,但实际上还是谈观念层面上的事。”皮力说。


“洞穴”系列作品,2018,展览现场图

《幻影》,2018,展览现场图
刘韡喜欢,而且总是用廉价的材料—金属、木头、镜子、书本、海绵等废旧材料,用最平凡的材料和词汇创造新的意义,一如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所说:“一种独特的意识贯穿了刘韡的整体创作,即物和材料的交叠是如何产生意义、物在空间中的位置是如何建构观众的体验的。”他用这些廉价材料构筑让人联想到城市的建筑景观和教堂的建筑样式,或者在画中“预设”一个类似城市景观的图像底本和经验基础,而后利用电脑软件进行形式的分解、重组和描绘,刘韡认为这与城市这个命题相关,“我会去看一个城市的发展,理解整个制度,城市本身就是人类一个最伟大的体现,它体现了所有的文化政治。”他观察,并从日常的视觉经验中抽取他想要的部分,再加以改造和整合,让观者从中联想城市里斑驳的、奇异的、疯狂生长的风景。

▲刘韡工作室一角
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风景,那些充斥着阶层、贫富冲突与对立、始终变动着的风景。迅猛的城市化运动几乎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城乡结合部就是这一社会变动的直接产物。“那是一个连接城市和农村的裂缝,他们的生活状态既不工业化,也不全球化,所有的东西都恨不得自己做,就像艺术品一样”,日常所见所感成为艺术时间的素材和动因,因此,他回收这片“风景”中的剩余物,社会生产和艺术家的创作再也无可分割。



《幻影》,2018,展览现场图
“你做的东西,不可能逃出你看到的东西。”刘韡说。“这儿生活着社会末梢的人群,也是我们真正的现实,它们混乱嘈杂,聚积着来自于全国各地身份不明的打工者,滋生着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刘韡指的是环铁,他从 2006 年就在这里建了工作室,中间更换过一次地点。如今 2000 多平方米的工作室中,办公、会客、储存、创作空间一目了然;在工作室里,他提供清晰的工作原理和思路,其他都交由工人去实现,“基本就是有一个计划,很兴奋地告诉所有人,然后开始实施;第二天,又有一个想法,于是之前的全部推翻”,刘韡在展览前的工作状态,就是“尽量把自己逼疯”。在制作大型装置时,他常常提出一些对作品色彩、体量、形状等的具体要求和规则,让工人们在遵循这些复制原则的情况下自行制作;而绘画作品均由刘韡以电脑制图为基础,之后再将数码图片转为架上绘画,“画画对我而言是一个太享受、太自我的事情,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到那种状态里;我觉得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与精力每天陷入到绘画的快感中,我必须要把自己解放出来。总之,我不追求绘画的‘手感’,也不需要它们出现在我的作品里。”绘画、雕塑、装置、影像……尽管刘韡不用自己“动手”,但他依然对一切进行把关和控制:“对我而言艺术的终点是最重要的—一件作品在哪一刻停止”。

▲刘韡,《谜中谜》,2014,综合材料装置,尺寸可变,展览现场图,Blaise Adilon摄,里昂双年展,2015
“我对于艺术能够在什么层面上与生活以及社会发生关系非常感兴趣,这关于如何能够真正地将艺术与现实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如何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展示这些作品。就这么简单。”刘韡说。“对我来说,削减是唯一可能的创作方法,或者说是我的主要创作方法。在创作时,
我不做‘加法’,不在形式上进行添加,而是要进行削减,而形式本身也是由环境或语境所决定的。”他说他讨厌情节和故事,希望建立更抽象的逻辑,希望让逻辑成为叙事语言。


《气流》及其局部图,2018,展览现场图
“削减的过程是靠添加知识来完成的。”他“用知识剥落”的作品,包含了环境恶化、充满权力和政治色彩的历史、诱惑与憎恶并存的当代城市生活主题,记录着文化焦虑心境下对情感过剩的反思。于是,他的展览也以空间组织方式被转变为某种艺术作品的叙事经验。“我在做展览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要什么,把不要的东西全部丢掉,剩下的可能就是我想要的。我每天推翻一些东西,到最后很大一部分是依据整个展览如何给观者更好的感官传递。其实整个展览像是一件作品,最终每一件作品消失了,变成一个展览的概念。”


《周期》,2018,展览现场图
他还在强调创作中幽微的不可言说,“把所有吸引你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你的观点。”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无法预料最终的目标,但他知道什么“不可为”,于是,他的艺术实践更多地如鲁明军所描述的,“来自一种限制,然后尽最可能地剔除他认为的那些无法嵌入现实的元素,直到一个无法再剔除的临界点”—刘韡所谓的“真实”。


展览现场图
刘韡曾说:“一件作品之所以有生命,就在于它尚未被观者彻底看清的部分”,这颇富哲学意味:“只有一个物体在不完整的时候才是完整状态,完整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样的他,喜欢法斯宾德、帕索里尼的电影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他也喜欢《星球大战》系列,“浩瀚的宇宙景观就是无穷的资源,在其中,什么都能谈,它是一个无限生长的体系。”—但他也自曝喜欢《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这种自相矛盾的喜好是否也呼应了他的富有斗争性的创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