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歧路听桥

1989年11月10日,东西柏林交界处的勃兰登堡门,西柏林民众在这里的柏林墙上方值守。此前一天,东德政府开放了这里的边界。图片出处:rarehistoricalphotos.com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SI)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图:Noah Berg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福山(大多)说对了
保罗·米勒(Paul D. Miller)
众所周知,三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冷战的终结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风行四海”。
当他宣告“历史终结”时,他不是在预言未来,而是在宣告一项判决:历史业已表明,征诸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见的尺度,自由民主都是最成功的统治形式。对关乎人类文明目的(或者具体从哲学上讲,叫“终极目标”)的诸多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已经有了答案,而这一问题至少自柏拉图写作其《理想国》以来,就刺激着人类开悟的好奇心。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早已终结。
福山对“历史终结”的论证而非夸张描述,依旧令人信服且强悍有力。自由民主不存在可以想见的意识形态对手,他的这一观点依旧掷地有声:尽管中国崛起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崛起而后败落了,俄罗斯回到黩武状态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正席卷全球,但可与自由民主相提并论,且具备普遍愿景和全球魅力的另一整套政治和经济主张依旧付诸阙如。
假如福山遗漏了什么的话,那可能是,我们正见证福山所指出的对“历史终结”的所有三大可能挑战的合流,即怀旧情绪与宗教基本教义派和民族主义力量的合流。包括普京的帝国复仇主义以及圣战和民族主义梦想的持久吸引力在内,这些现象的结合似乎正在策动指向自由民主秩序的广泛挑战。后历史时期的怠倦之感刺激和策动着这些力量,它们充当了自由主义的寄生虫:有赖于,同时侵蚀着自由主义秩序。
解决之道或许是,自由国家后撤,并为社会中的前政治性组织——家庭、宗教机构和民间社团——留出更多空间,以活跃和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只有这样一些组织,才能祛除导向政治和宗教迷狂的人类天性冲动之毒。(以上及以下有关福山观点的引文均出自“The End of History?”一文,载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引号中的“历史终结”在原文中均为首字母大写,下同。——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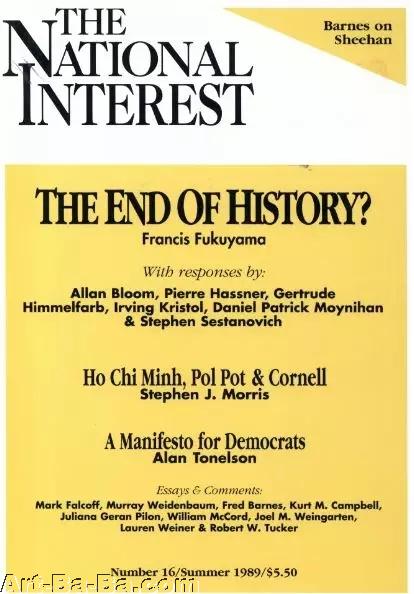
刊登《历史的终结?》一文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图片取自jstor.org。
福山说了什么
福山深具原创意义的文章涉及对政治理论的重要讨论,而非未来主义,这令一些批评家惊愕不已,他们一度想将他的文章视作精心打扮、世俗化版本的末日启示论而不屑一顾。
福山还小心限制他的论证:“历史终结”并不意味着“不会再有事件来填补《外交事务》的国际关系年度概要版面了”。他也没有暗示,每个国家都将立刻向自由民主转变:“到历史终结时,不是所有社会都必定成为成功的自由社会,而只是,它们不再假装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代表不同且更高级形式的人类社会。”
“历史终结”也不意味着战争的终结:“这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国际冲突就其本质而言的终结……恐怖主义和民族解放战争将继续成为国际议程中的重要议题。”冲突会继续,很多国家会依旧存在于“历史”(History)当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时候,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可能作为自由社会,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之列”,他写道。与此同时,发展中世界“依旧深陷历史的泥沼,未来多年后将成为冲突发生之地”。不是所有国家都将意识到或者欢迎“历史终结”,这多半是因为自由主义威胁到了非自由主义精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几乎总是富人,来自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或者宗教团体。(引号中的“历史”,在原文中均为首字母大写,下同。——译注)
再者,福山的文章为地缘政治竞争和政治对立状态的延续留下了充分的空间。1989年,他特别强调指出,两大社会和政治运动可能激发持续的冲突:民族主义和宗教基本教义派。尽管福山对未来的洞见并不完美,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宽泛的勾勒看上去相当面熟。
民族主义
在其最初的文章中,福山对民族主义的态度相对乐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民族主义已被祛除毒性,与外交政策的真正关联也被切断,结果是,十九世纪的大国行为模式已经成为严重的时代错误。”
这一冷静的看法部分源自他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区别:前一种民族主义是“温和的文化怀旧”,他意识到这种民族主义依旧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后一种民族主义是一种“高度组织化”且“精确阐述的学说”,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早已声誉扫地。他还认为,民族主义既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回应,也不是对自由主义之失败的回应:假如各民族确实如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希望的那样,是独立且自治的,那么民族主义者也就不必诉诸非自由主义和危险形式的民族主义了。
福山在1989年也许是对的,但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没有描述普京、欧尔班(Orban Victor)、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和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这样一些人,更不要说玛琳·勒庞了。民族主义生机勃勃,似乎远不只是“温和的文化怀旧”。特别令人忧心的是,在匈牙利、波兰和巴西这种初具雏形的自由民主国家,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回潮了,这似乎证明了福山如下看法的落空,即自由主义可以祛除民族主义之毒。甚至唐纳德·特朗普、纳伦德拉·莫迪或者习那种(相比较而言)更为宽厚仁慈的民族主义,都无疑与二十一世纪的外交政策相关,也可能重又恢复了毒性。(欧尔班是现任匈牙利总理。卡钦斯基是保守派的波兰议会最大党“法律与公正党”主席。博尔索纳罗是巴西现任总统。玛琳·勒庞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译注)
但即便是在1989年,福山似乎就意识到民族主义复兴的可能。他论及普京崛起之前十年的俄罗斯:“在苏联,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趋向相当强烈……苏联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极其相信他们的亲斯拉夫事业。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在那里,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替代思潮并未完全退场。”普京对苏联时代荣耀的钟爱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恢复使用了以往苏联国歌的配乐,用作新的俄罗斯国歌,这是福山怀旧情绪之说的教科书般的例证。
假如福山忽略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民族主义的怀旧情绪不只限于俄罗斯的例子。譬如,论及中国,福山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的行进轨迹。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业已见证马列主义作为经济体制的几乎彻底声名狼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再充当全球非自由主义力量的灯塔”。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端似乎显示,“政治自由主义一直在追随经济自由主义,追随的步伐固然较很多人曾经希望的要慢,但看似不可避免”。这显然是在暗示,中国最终也将步入民主转型阶段。但过往三十年发生的事实表明,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它变得更加民族主义,而不是更加自由主义了。
福山似乎不曾意识到其部分论证之间的张力。他驳斥了这样的看法,即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将回归沙皇或者帝国时代的外交政策,但后来又描述过那种驱动国家回到历史王国的怀旧情绪和历史渴求的力量。过去十年间,恰恰是这种怀旧兴趣指引普京在邻近国家推行新沙皇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而且,普京不时试图改造其威权政体,不只是谋求俄罗斯军火的粗鄙荣耀:由此酝酿中的一套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正设法向发展中世界输出。假如取得成功,这些举措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将民族主义改造为“历史终结”的全球性替代品。
宗教基本教义派
福山预言的第二项挑战是“宗教基本教义派”,这个例子更加错综复杂。福山承认,宗教具备一种持久性的力量,且宗教与世界事务的关联在更加传统的分析中往往被忽略了:“宗教复兴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人们对自由主义消费社会的非人格化和精神真空的广泛不满。”福山对宗教的同情,可以部分解释他何以能意识到后历史时期的倦怠之感和渴求的危险(详下)。
他一方面认为,大多数宗教似乎都与现代性实现了和解,且不大可能对自由主义构成挑战;同时正确指出,“在当代世界,只有伊斯兰教提出了神权国家,以之作为一种政治方面的替代主张”。但终究,这种神权的(或者圣战的)替代主张“对非穆斯林绝少吸引力,也令人难以相信这场运动将呈现任何普遍意义”。不论恐怖主义有何种动机,他都不屑一顾:“我们的任务不是透彻解答世界各地每一个疯子救世主发起的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挑战,而只会解答那些体现在重要社会和政治力量和运动中,因而成为世界历史一部分的挑战。”
本·拉登、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和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确实是疯子救世主(更准确而言,是疯子教主和哈里发)。但对他们从事的运动不屑一顾,仅仅因他们的诉求从来没有普及四方而不认可它们是世界历史的真实一部分,似乎难以令人满意。福山解释说,他只对“人类一般的意识形态遗产”有兴趣,这是他何以会说宗教基本教义派和恐怖主义不是“世界历史”一部分的原因。(扎卡维生于1966年,是约旦圣战分子,2006年6月在伊拉克被美军击毙。巴格达迪生于1971年,是军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最高领导人,可能仍然在世。——译注)
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们对普遍性主张提出的挑战:借由反对普遍性,它们差一点就一统世界了。特别是考虑到福山坚称,意识形态的演进,辩证地受到对某个他者的反对的驱动,也部分有赖于这样的反对,那么圣战运动(jihadism)理当作为一种终极他者,一个与自由主义旗鼓相当的对手,而受到承认:这个对手有如法西斯主义一般,通过凸显其对立面,帮助证明和判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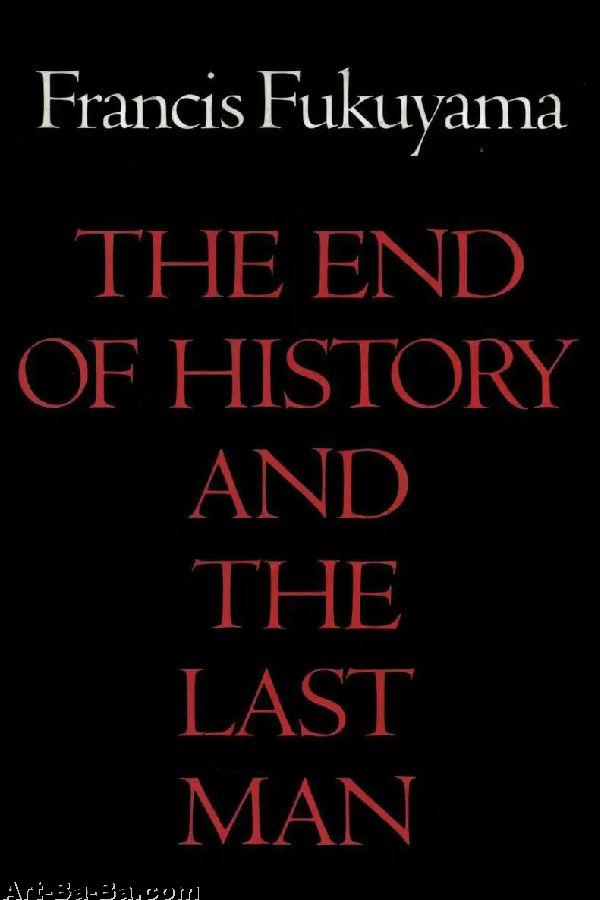
由《历史的终结?》一文扩充而成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年英文初版封面。图片取自英文维基百科。
“历史终结”的缺憾
假如民族主义和宗教基本教义派未能充当自由主义的竞争者,那么我们终究或许可以庆祝“历史终结”了?饶有兴味的是,福山似乎并无此意。
对“历史终结”最常见的误读可能是,那意味着庆祝自由主义的大获全胜。人们有时记得福山的文章,是认为其傲慢自大或者不合时宜,是在1990年代初那种令人陶醉的氛围中写就的受到蒙蔽的狂想。该文被认为略令人反感,像是冷战胜利之后的大肆庆祝。
事实上,福山是在1980年代末写作该文,当时柏林墙尚未倒塌,更不要说苏联崩溃或者海湾战争了。他不知道迫在眉睫的诸多事态会推动他的文章,令该文名声大噪,并将那个标题(略去问号)变成了一个梗。他的文章并不包含庆祝大胜的语言,且满是告诫和保留意见。最重要的是,福山是以极其沉闷的语调得出结论,乃至于三十年后,因其悲观色彩,不幸的是也因其掷地有声,这样的语调简直令人震惊。
“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极令人悲哀的时刻”,他写道,对这一时刻“我的感受最为矛盾”。他为人类英雄时刻的逝去而痛惜:“矫揉造作的消费者需求获得满足……将取代谋求承认的奋斗、为一个纯粹抽象的目标而蒙受生命风险的心甘情愿,以及呼唤关爱、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的全球意识形态斗争。”历史已经终结于郊区整齐划一的预制行车道。“在后历史时期,既不会有艺术,也不会有哲学,有的只是对人类历史博物馆的永久看护。”
福山回应了现代性的批评者,他们悲叹小资产阶级的兴起,因为这些人缺乏格调和文化。一个半世纪之后,托克维尔警告说,因为自由民主的兴起,“生活的多样性正从人类社会消失”,每个国家的人都越来越多地完全放弃了本阶级、本行业、本家族所固有的思想和感情,一起变得更加接近到处都是一样的人的本质。”
在那些平淡乏味的同质条件下,自由社会中“所有那些有时令人目眩,但往往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的慷慨激昂的德行,都将被这个国家的人民视为等而下之”。对托克维尔来讲,失去那些“慷慨激昂的德行”有真正的危险:“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人们不断忙于私人生活的琐碎小事当中,奋进之心可能失去其推动作用和崇高目标;人们的激情既没有昂扬又没有低落,结果使社会一天一天走向看来十分安宁但缺乏大志的状态。” (以上两段中有关托克维尔的引文,分别取自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三部分第十八、十九章,结合本处原文略加调整。——译注)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福山认为,托克维尔的担心已经发生了,所以他警告人们留心“对历史存在之时的某种强大怀恋情绪”,这种情绪是对“历史终结”的第三项挑战。
或许,没有奋斗,人类就无法存在。“事实上,甚至在不久之后的后历史世界,那种怀旧情绪仍将继续激发竞争和冲突。”福山暗示,“历史终结之时会出现数个世纪的无聊,如此前景将推动历史再度前行”,这是最具先见之明的看法。
的确,如此后历史时期的怠倦之感,几乎可以肯定是绵延不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诉求的驱动力,但福山似乎忽略了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之间的关联,尽管他在其近著《身份》(Identity)中并未忽略这一点。《身份》用一定篇幅讨论了“人类对高人一等的地位的欲求”(megalothymia)。驱动后历史时期怠倦之感的,是对承认和英雄气质的渴求,即对一个男性可以完成伟大事业(梦想着危险的壮丽和恢弘之梦的,确实似乎主要是男性)的时代的怀恋。福山提出的这一强大的心理影响力几乎无可避免地似乎与宗教和国家组织相关,它们给我们带来了多种形式的宗教和政治狂热,而这样的狂热威胁到历史的终结。
民族主义和宗教基本教义派是对现代性状况的并生反应:它们都属于政治神学,谋求将我们的所有忠诚纳入到一个单一的、主导一切的有机政体庇护之下。民族主义者、惯于煽动民情的政客和狂热分子之所以为了他们的事业而乞灵于往昔的历史神话和象征,是有原因的。民族主义者将自由主义及其在“全球政策”中的延伸,视为一种对民族身份的瓦解,一种对他们独特历史、传统和文化的拒斥。普京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往昔苏联和沙皇时代最多的共鸣。圣战者看到了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模样,视其堕落、不纯而加以拒绝,转而倾力复活他们所(不准确)认定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历史纪元,他们认为那是伊斯兰教的至纯时刻。甚至唐纳德·特朗普也想重振美国。
历史讲述了一个有关我们是谁的故事,一个通常满是冲突、奋争甚至是暴力的故事。假如你告诉人们说,历史已经终结,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去奋争,你就是剥夺了他们至关紧要的身份的来源和目的感。福山的悲观洞见在于,人类将为身份和目的重建某种基础,即令那意味着再度陷入冲突和黑格尔式的大写“历史”之中。
在美国,在个人层面,我们或许看到了同样的心理现象:不然,如何解释许多年轻白人男子似乎是受到什么驱使,制造了显然毫无意义的集体杀戮事件?现代社会忽视了他们,而自由社会告诉他们,随着他们长大成人,他们从电影和历史书中学到的,并认为对他们的身份至关重要的尚武之德,比一无所用更糟糕。他们是危险的。受到狂热情绪奴役的民族和宗教对历史终结的威胁,或许不亚于虚无主义的尼采式无政府主义者。
福山说对了吗?
假如自由民主在精神层面极为空泛,乃至于会激发向往昔民族主义和宗教狂想的回归,或者未来的无政府主义,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福山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如何分享这样的看法: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是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最优安排,它们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过去三十年,自由民主经历了诸多挫折。即便如此,温斯顿·丘吉尔的论断——除了其他所有形式之外,民主是最糟糕的一种统治形式——依旧难以改进。过去三十年或者三十个世纪中,没有出现更具说服力的反驳。自由主义的每一个替代方案都等于是宣称,有些人天生就有权统治其他人,这通常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信仰、勇武、虔敬、爱国或其他什么事情上高人一等。这样的主张不论如何包装,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话。这样的主张一再造就这样的社会:更不自由、更欠繁荣、更缺活力,本质上更少人道精神。
自由主义的伟大洞见在于,人类——他们中的所有人——天生就具备价值和尊严,仅仅因为他们是人。容易被忘记的一点是,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中,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大多数社会并不同意这一洞见。所以值得重复:没有人可以天生就因其出生、血缘、位阶、财富或者任何其他属性而高人一等,值得政府特殊对待,或者拥有获取权力或者财富的特殊渠道。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安排是围绕这一洞见而构造的。
正是这一基本起点,将自由主义与君主制、贵族制、寡头制、独裁制、神权制和其他等级森严、非自由主义的统治形式区别开来。天主教哲学家帕特里克·迪内恩(Patrick Deneen)最近提出的高见涉及“自由主义何以失败”。但甚至是他这样自由主义的最严厉批评者,也没有否认这些断言,或者另外提出一套有关人类价值和尊严的主张。就此而言,福山完全正确:建立在平等且不可侵犯的全人类尊严这一基础上的社会,优越于那些不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帕特里克·迪内恩,现任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自由主义何以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是迪内恩的一部专著,201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译注]
如何守护历史的终结
假如自由民主不论好坏,仍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佳政治选项,那么其失败和目前的危机有解决方案吗?不幸的是,福山在其最初的文章中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三十年过去了,改造并强化自由主义以对抗其挑战者,成为格外迫切的需要。他认识到“自由主义内核的空泛,最无疑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缺憾”,但也承认“(这样的空泛)通过政治活动可以补救,这一点完全不清楚。”
至少有一个答案显而易见:捍卫自由社会免遭其对手的侵害,依旧有赖于英勇的德行。战争依旧到处可见。假如2001年的恐怖袭击或者与朝鲜的一场战争依旧可能在“历史终结”时爆发,自由社会依旧有必要培养尚武之德。捍卫自由主义秩序理当被视作高贵甚至是英勇的追求;碰巧,捍卫自由主义秩序同时是一道安全阀,为那些不满于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的庸常机会的人提供了有益的事业。
但这无法为自由主义在精神层面的空泛提供彻底的解决方案,无法回应大部分平民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等同于将自由主义维持在对其敌人嗜血杀伐的基础之上:假如放任这样的杀伐蔓延,这将为民族主义和狂热行为而不是为任何它们的替代方案提供捷径。
困境在于,我们最重大的诸多政治难题的源头是前政治的。对政治家和选民来讲,这是难于接受的真相。作为启蒙运动的后人,我们已习惯于从诊断一个问题直接转变到提出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坚定地认为,人类的理智可以理解并减缓这个世界的弊病。特别是,遭遇公共或者政治难题时,我们会本能地转向国家,以帮助资助、协调和执行我们的解决方案,因为,依据启蒙运动的理念,国家就是做那些事情的。
这怎么可能成为难题呢?假如我们最重大的诸多政治难题的源头是前政治的,当启蒙国家介入,帮助解决那些问题时,国家就不再只是谋求维持秩序、实施正义或者克服集体行动难题,它转而要在人类境况方面实现永久的改变。事实上,国家成了替代性宗教:不只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圣战运动这样一些明显的政治性宗教是如此,进步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样一些更加仁爱宽厚的运动也是如此。尽管据认为它们的抱负更加安全无害,但进步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力求将不具人格的政治组织转变成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格化共同体,以填补自由主义在精神层面的空泛。
倾力于这一任务的国家令人失望,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政治方案无法解决前政治难题。对一些人来讲,随之而来的不满将刺激他们再度致力于击败他们的国内对手。在谋求政府更进一步展示绩效的过程中,他们成了政治狂热的牺牲品,这导致了目前在美国依旧存在的那种政治极化和激烈的党派之争。对其他人而言,令人失望的现况导致他们彻底拒绝政治,而以宗教取而代之。但在如此情形下,宗教被拖入了与政治抗争的战场,因而会模仿国家的抱负,这会催生宗教基本教义派和神权政治的野心。最终,少数其他人将以暴力手段拒绝国家介入他们的生活,这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
在每一种情形下,当国家试图解决前政治难题时——当国家谋求矫正内在于人性的心理和精神状况时——它都会逾越自己的边界,引发“历史”力量的强硬回击,于是,局面通常以恶化国家谋求解决的那些难题而告终了。
解决之道或许在于,自由国家重新定义其角色。启蒙运动之错,在于将国家变成了——用霍布斯的重要术语来讲——“活的上帝”(mortal god),因为这样一个个上帝无法兑现其全能的承诺。国家最好承认,它是维护秩序、正义并展开集体行动的工具,仅此而已。
有这样一些组织能够直面人类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家庭、信仰共同体和民间社团。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样一些组织对保持民主社会的活力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才能焕然一新,胸怀才能开阔,才智才能发挥。”他写道:
“一个政府之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去维持和改进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正如它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去管理每一个实业部门一样。一个政府,只要它试图走出政治领域而步入这条新道路,它就会不知不觉地要实行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暴政,就算它并没有打算这么做。”(以上两段中的引文取自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五章,结合本处原文略加调整。——译注)
一个希望在“历史终结”之时捍卫和维持其成就的自由政府,或许有必要学会后撤,并确保这些非政治性的组织繁荣兴盛。强大的家庭、教会、犹太教堂、清真寺、体育俱乐部、新闻媒体、文学社团、观鸟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以及男女童子军,都可赋予自由社会以弹性、精神上的成熟和深度,这些素质是抗拒民族主义、基本教义派和怀旧情绪的诱人召唤所必须具备的。当然,如任何介入这些组织的人士所知,这远不止意味着看护人类历史的博物馆。
我们不会无聊或者精神空虚到了按捺不住诱惑,要去重启“历史”的地步,因为我们会用关爱家庭、朋友和我们所爱的人,来充实我们的每一天。
(作者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荣誉教授。本文原见于《美国利益》杂志网站,2019年1月14日发布,原题:“Fukuyama Was Right (Mostly)”。除第一张有关柏林墙的图,其余图片均由译者配发。个别段落有重新划分,人名有调整。听桥译,祈请方家指正笨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