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科幻是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安慰(上)

2001: A Space Odyssey
--评斯蒂凡.瓦勒DR.STEFAN WALLER的9月7日国美演讲《技术作为人的图像》
理论车间于2015年9月18日
一、技术是人用来安慰自己的图像
演讲者斯蒂凡·瓦勒从阿诺德.盖伦的技术人类学角度向我们发问:人与技术的关系,为什么不可以从情感(最广意义上)上加以考虑呢?技术这不就与艺术同域了吗?也许技术与艺术之间的相近比我们想象的还相近?
这是说,从情感依赖的角度,人有可能是将技术当作一个关于人自己的更大、更可靠的图像,将它当作依靠,来获得安全感,减轻人自己身上的生存压力的。比如在远古,一个动物石像会被做得大于人的尺寸,来被膜拜,人才从中找到了安全感,神意也就从这种“大”里冒出。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有艺术的功能:给人衬托,帮人卸下一些自我防护的担子,使人脱开身,甩开膀子去改造世界。
在今天,手机的尺寸是小的,但我们与手机之间的关系,仍典型地反映了上述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社会对我们分分钟都不可靠了:但我有了手机!它百分百让我胜券在握!它是我的司令部。哪怕我不小心迷路到火星上了,它也可以帮我呼叫总台、总部。所以手机体积虽小,却仍在另一层面上说大于人,比人更牢靠,人在感情上就这样依赖于它来定位和被扶慰。我们对于雕像,对于纪念碑,对于艺术作品也一直是这样去寄托的,是要去建立一个比人更大、更牢靠的东西,拿作我们情感上的靠山。它大于我们,我们可以靠它获得慰藉。情感上的事说不清,但反正只要有了这个技术产品或艺术品,我们也就消停、妥贴了!艺术品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也就是干这样的!挂那里,就起这个作用!没有它,我们就觉得缺了什么,但到底具体缺什么,我们自己也是说不出的。
那么,手机到底是人的图腾,还是人本身?在开拓这个认识上,斯蒂凡所动用的技术人类学是有局限的,我们得引入另外的眼光来进一步扒开这个问题。当代法国哲学家马勒布说,手机代表了人的当前状态,意思也就是,是手机更好地代表了人这种技术式成为的当前的最真实状态,而并不代表那个去对手机作出判断的“人“的目前进化水平。手机是人本身的当前的技术式成为的真实状态的明证(蒸汽机、汽车、收音机、电脑、智能手机)。两年前的苹果手机不是了,但这个月刚发布的那款苹果手机,可以说,就是这个我们共处的时代里的“人本身”的真正代表。我不能站出去我自己代表了人进化的某一阶段的。斯蒂格勒的“人就是技术”这一句,也应被这样理解:像苹果手机这样最到位、最普及的技术,就是我们说话的这一刻的“人本身”,这就是了,而不是其代表。
不过,人是将技术当作假肢和药罐来用的。人是依附在它上面,被它引领的。这是目前对于技术之形而上学化解构得最彻底的一种立场,斯蒂格勒称此之为技术之“逆人类学”(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就是西方的思变成形而上学后的恶果;技术本质是好的,但西方人不会思了,技术就成了捕捉、革新和营销。二十世纪人类学也将技术看作是替罪羊,看不到人是会双面(既当假肢又当药罐)地使用技术的)。而斯蒂凡动用的盖伦的技术人类学里还存有关于“人”本身的幻觉。我们必须考虑到人类学本身在当前时代的严重局限性。
但是,我们可进一步问:手机不来,会有别的同样精密的假肢来替代它的吗?一定会有的。没有,那我们也会原路退出,另寻,一定能找到另一种的。我们会像做石像、画油画和做装置那样去发明新工具、新机器,来响应我们当前的需要的。我们总能达到目标。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地“够用”的。法国科学史学家Gill说,每一个时代都会达到与其相称的技术条件。这就像再穷的民工也能安顿出一个温暖的家一样。意思也是,技术对于某个时代的人而言一定是刚刚够用的。人与技术之间总是达到了这样的一种既共生又互补的“对话”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当代人常会显得傲慢。在今天,后一代人会经常瞧不起前一时代的人的技术-媒体局限,以为我们看清了他们没看清的,并看得更远了。这是幻觉。其实是,不同时代的技术状态提供给人的可能性(媒体),是一样多的。后一代人是在另一种技术式成为中去看前一代的了。我们可以嘲笑前代人不懂,但他们的不懂,在那时代也曾是一种丰满和自足的知。我们每一代人都被限制在完全不同的媒体里,不同时代的人动用的是完全不同质的技术-媒体来叙述自己的故事,从哪一时间点上都无法评断后面是不是比前面先进。十八世纪的人不可能给我们录像证据,二十世纪的人虽会提供,但很有可能,他们提供的是弄虚作假的影像。每一时代的人又被他们自身的技术状况所局限,后一代人用他们自己时代里的媒体去理解前一时代,一定是生硬和暴力的。

其实,我们对于前代人的技术-媒体局限的看法,压根就是暧昧的。比如,我们既从老照片里看到了其粗粒和其所指的被架空,同时却正因为它是老照片而更会借以怀旧!
总之,还必须给斯蒂凡的立场里加上这一点:人被它自己的图像也就是技术局限于某时代,这过程同时是假肢式和药罐式的:能靠它获救,却也能因此沉沦迷醉。技术除了是人类自身的图像,作为第三存留,也是人的生命的进化的支架。我们人的生命就像海里的牡蛎,是爬在技术这根木桩上才能生存和成长的。但一外化,就会中毒,就需要长期消毒。盖伦的技术人类学未及这方面的思考。
二、科幻是人与技术之间的一种对话过程
斯蒂凡强调的盖伦的下面这一立场,值得我们重视:技术是人对自己提供的关于它自己的图像。他从黑格尔的“会客观(对象)化的精神”这一角度,将技术解释成了“镜子”:技术倒过来反衬出人是什么。在科幻片中,技术反照出了人将会是什么和怎么应付未知环境。上面已部分说及,手机同时也是“关于”人的图像。手机中映出当前的人的全部情性。而看科幻片,是人在观察被放入实验状态的人自己的行为。外星人到地球来研究人类,与其研究其解剖特征,还不如研究它的苹果手机,正是这个意思。
这是他的这个讲座打开的一个很重要的面向。我们从这个立场中可推演出:科幻是人做给自己看的,是人将实验搬到了自己身上而开始的一种自我观察和自我思辨。在现实里,我们会看不清自己。我们于是将自己放在未来之中,让自己变形,于是就能连续地一次次看清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了。而根据盖伦的技术人类学眼光,在今天的技术飞速发展过程中,人虽然有了那么多的装置,但仍却会有科幻片里的主角的感受的:一切都已失去了功能,需要有全新的技术来力挽狂澜。科幻片里的场景,比起我们人类的新技术处境,其实还是相对不“科幻”的呢!你去看看肯德基柜台前一个少女拿出手机找二维码拍下显示要求给炸鸡腿打折的情景,那不是更科幻吗?优步和陌陌颠覆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谱系,如此离谱但仍得刷卡付费,不是比《盗梦空间》更科幻的吗?科幻片其实像一张极其美妙的沙发,多放松!而且,最主要里面的事物很少与收款处相关!真的,在科幻状态,我们会发现,由于抽掉了日常利比多经济,里面的故事和气氛就特别有温情。
如今的时时地在现实中被推入科幻片情景之中,这是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人的一种躲不掉的处境了。许多人都这样理解,正如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很多左派思想家所理解的那样:人被技术操控,被动和异化了。技术像科幻片里的恶魔。这种感觉大错特错!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科幻和科幻片中,科幻的开始处恰恰是现有的技术装置和机器开始不灵时。如果一切都运转正常,我们是不异化的,而是很“人”、很“人”的。就如库布里克《2001年漫游太空》里设备全部正常运转,飞船驶向太空的那一刻,人们虽然在奔向可怖的太空,在太空舱里的人应该是最异化的(照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来理解)。但驾驶室里放的却是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在太空中,人才更“人”了!能克服更多的技术困难的人,才更“人”!只有能克服琐碎的技术问题,放心地驶向外太空的人,才是自由的。而自由从疏离中诞生。黑格尔的知识:人从它所处的环境中疏离出来,保持距离,才能升华自己;当升华后的人重新进入其环境后,人变了,那环境也变了,这时,人才开始生产新知识,才得到新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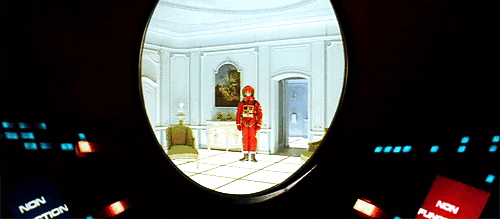
2001: A Space Odyssey
反面就有科波拉的《启示录之末日之战》里美军直升机飞行员听着瓦格纳的《唐豪塞》序曲扫射越南村庄,也是!你可以说,那时,在所有机器运转都很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是更“人”的!而“更人了”,是可以很可怕的!
是的,我们看到,在科幻片的开头,人原有的技术和机器和人类制度全都失效了!总是需要制造出新的设备去对付外星的敌人。这幻觉是基于弗洛伊德们所说的人出生时就带有的易受伤害感,是人无意识里带有的关于生存的根本处境的情愫。人的生命得找到那个外部支架,才能幸存;对于天体物理博士,他们得找到他们的太空舱,才能感到安全然后自我实现,要他们在地上成为人,就有委屈了他们。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和关照,生命才能技术地变形到很灵怪的程度,才自我实现。所以,科幻片的开头,在政治上说,是很激进的,它将人带到了这一原初处境中,什么都不灵,人开始挣扎,可以自由地成为意想不到的一切…
三、科幻是人本身的技术式变形
机器人只是人的技术式变形的一个阶段,中间充满变数,人处于卡夫卡《变形记》里的主角位置。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是人的假肢的联合。它是更脆弱和“单向度”的人。讨论到人工智能和人的需被启蒙状态时,斯蒂格勒搬出了康德:启蒙是要使人达到成年人的不需要被监护的状态;但人不是上帝,不可能时时都像成年人那样聪明。人是一种亚里士多德说的noetique(感-知)式存在,需要大多数时候沉沦在愚蠢里,只能在某一刻钟里聪明一下。很多时候,是人的愚蠢救了人。人必须守在其愚蠢里,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艺术的道理。制造一些机器放在科幻片里,让机器人出手,人就可以更好地呆在自己的愚蠢里。这里又可看到艺术与技术的分野:根据盖伦的技术人类学,人工智能的技术装置和艺术作品,是人制作的同一种东西的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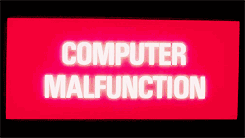
但我们都知道,一架机器人要能维持正常运转,其实需要一个庞大的工程师团队和九、十位数的拔款。看上去,机器人太厉害了,但成本却是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的浪掷。但尽管如此,它却连自己最基本的自理如加机油、开和关和自身卫生的打扫,也都要劳烦车间阿姨,就像一个陈景润在我们的队伍中,为了让做他做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用的算术,得有那么多人围着他转。
所以,在讲座提问中,很多同学的关于技术或机器人要是比人还聪明了我们人将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既形而上学,又属于受迫害狂想,是提了假问题!斯蒂凡的回答也太暧昧,没说清这一层。其实他应该这样回答:是人要机器人比人聪明的(人想要呆在自己的愚蠢里是真,但它什么时候想要走出愚蠢,分分钟都能做到)!是人要人工智能来战胜人的,像它要“蓝色巨人”来战胜或败给世界象棋冠军一样,因为人很贱,这样折腾自己,才能达到自我认识。这就像讲故事时,我们一定要让主人公在紧要关头差一点打不过里面的恶棍的原因,但一定仍要在最后关头让它胜利,或弄成悲剧,表明我们观众是知道它错在哪里,其实打败那个敌人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我们只是要测试一下我们人自己的韧力和弹性度。
要是有一天机器人真的比人还聪明了怎么办?这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恰恰是盖伦说的我们人类需要技术的原因:我们要把自己对象化到科幻片里的人类紧急状况里。我们竟想:让那个更能干的自己—机器人,来拖着一个不大能干只会恐惧和哀叹的我们自己往前走。意思是:那个比人聪明的机器人在那里,我们要它当拖车,让人类这架熄火的车重新发动起来!而实际上,该问的却是:富士康这样的机器人工厂和自动社会里,人应如何去阻止自己被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失去其制作、生活和理论知识。决不是机器人来欺负人类,而是机器人使人变得无能,成为技术消费中的无产阶级一族,才是值得我们担忧的。
所以,对于那个机器人会不会来统治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更好的回答应该是:在机器人聪明到能向人发号施令前,人早就先将它们抛弃,去投入另一个版本的机器人的研发。机器人的命运总是像《2001年漫游太空》里的Hal在电影后快结束时那样,像一个坏蛋临死前放出最后一招:突然表现得很脆弱,弱弱地向人类问:能不能不要急着关我的开关,一切都好说的,让我再为你们跑腿吧,行不行?
机器人是被人类的三心二意和朝三暮四打败的。

2001: A Space Odyssey
《2001年漫游太空》中的机器人Hal,名字取自莎剧中的那个被驯服的王子。他坏得很二,又有福尔斯塔夫这样的蠢虫当跟班。但现实、人事和战事却使他奇怪地成长为勇敢担责的第二梯队。电影中,这个Hal也越来越像李开复,非常克己,错误都是人类的了。它只为我们扮演“优秀”和“靠谱”了。但导演库布里克反讽了:是的,聪明的机器人甚至能学着中国的公知腔了:素质,素质,你们人又错了;但机器人永远不会知道的是:正是因为人会错,才成了人的最后防线,人才是人,不能是别的。机器人Hal最后发现,学会人的不可解释的愚蠢和怕死,其实是最难的。
(待续)
金锋工作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