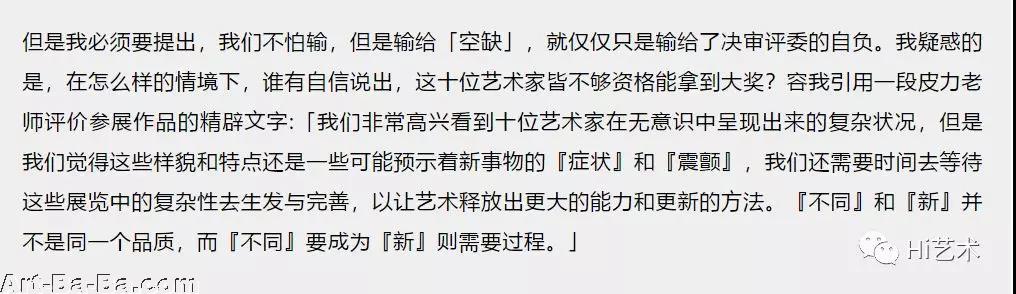来源:Hi艺术 周婉京
2020年1月1日,这个十年的第一天,微信公众号United Motion推送了一条名为《关于但不止于空缺》的文章。1月2日,同一公众号再次推送《空缺的艺术家费用》,再次以“空缺”为题并升级了关于“空缺”的讨论。乍一看,教人以为是美国民主党弹劾共和党的宣言,又或者是法国工人民主联盟CFDT讨伐马克龙政府而发布的联署文件。然而事实上,两个“空缺”都具体地落在国内艺术圈的讨论范畴之中:一个指涉的是华宇青年艺术家2019年大奖空缺的事宜,另一个指涉的是青年艺术家在国内参展时事后未获得“艺术家费用”的情况。看似都与“空缺”有关的两则事件,前者准确来说应当算是“奖项从缺”,后者则关乎一个尚未建立起来且不知何时才能发展充分的艺术机制。
笔者在这篇小文中想厘清的并非两个“空缺”的本体性区别,也不想讨论权力是以何种结构施力于艺术家本身的。我想跟大家一起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看到两个“空缺”时产生如此大的反应?毕竟艺术家除了做艺术创作之外,还具体地活着,受困于他们具体的生活状态。
2019年华宇青年奖
不愿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夹缝之下
姚清妹在其“艺术家费用”那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环境让我们都如此无时不刻心存感激却又万分疲惫?”她能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跟她旅居巴黎有关。她与国内艺术圈保持着距离,这让她每次回国的时候通过对比法国艺术圈的生态,更感到触目惊心。年轻艺术家上升路径窄、发展缓慢、信息滞后,都加剧了他们的上升路径窄、发展缓慢和信息滞后。而这些恶性循环的问题在上一代艺术家那里(通常指千禧年活跃至今的艺术家群体),反映得远不如年轻一代明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5G来临之前,这个时代就变成以消费信息为主的生产型社会。新的办公室不再是一栋大楼,我们也不需要挤早高峰地铁来赶通勤——只要一个计算机荧幕或手机屏幕足矣。这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AI”,这个“I”也不再限于“智能”(Intelligence)的意思,而扩展到所有可以被传输的“信息”(Information)。这意味着,如果艺术家无法获取到最新、最全面的信息,就有可能被同僚甩开、被后起之秀超越。这不再是一个两块钱在美院门口买一本印象派大师或培根、弗洛伊德的画册,回家以后照着临摹就足够汲养的时代。看画册,远远不够快。哪怕你不买画册,一个月在北京生活下来,酒仙桥的单人间最便宜的也要3000块钱(而且这还是与室友合租两室一厅的价位)。如果想要精装修、小区物业靠谱、环境安静优美的,钱就没数了。这还光是住,再加上吃喝呢?按照每天都在798门口吃沙县快餐或重庆小面的标准,一天三餐也需要30块,一个月下来将要吃掉1000块。如果策展人、美术馆和机构负责人时不时来你工作室转悠一下,招待客人的钱又不能免。你总不能回回都带他们去北新桥,一人一碗卤煮凑合着了?哪怕是苍蝇馆子,在北京,吃一顿像样的也要200块钱。这样加加减减,再算上穿衣、公交、看病、购买材料的钱,一个月至少要有5000块预算,才能在酒仙桥附近做一个体面的年轻人。而且这个预算尚未计入谈恋爱的花销,这又得看你找个什么样的“神仙”了(此处的开销可以是咝咝的,也可以是哗哗的)。据笔者了解,大部分刚入行的艺术从业者,包括没签署画廊代理的“北漂”艺术家和自由写作者,都不具备长期、稳定支付这笔生活费的能力。从美院毕业的许多年轻人,头几年选择在艺考补习班教书。而从国外回来的年轻艺术家,总会麻烦另一个艺术家朋友介绍到彼此熟悉的海外艺术类留学机构,做的与艺术最有关的就是帮人改“作品集”(artist portfolio)。这帮年轻人本以为可以通过获得奖项而支撑接下来的几年创作,却随着这届华宇青年奖倏而“悬置”的大奖而再一次对期待中的“艺术家生活”失去了信心。在这个时候,任何人再假借艺术之名安慰他们说“未来是光明的”,都等同于是雪上加霜。如果还有人不识趣地拿着研究后结构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哲学书往上凑,非要跟他们秉烛长谈一下中国艺术圈的机制究竟是怎么一个特色资本主义的,这不是自找没趣又是什么?参展的年轻艺术家和联署的从业者之所以会引起情绪上的反抗(而非理论上的反抗),根源在于他们不希望活在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夹缝之下。“起初做艺术不就是有点小理想吗,艺术代表了自由啊。倘若理想跟现实是一样的,那不就变成了双重压迫?”这次入选华宇青年奖的一位年轻艺术家在事出之后对笔者说。我记得同样的话,在两年之前也听到过。当时,北京出现了一波艺术家迁居上海的风潮。许多从事新媒体艺术、时尚、传播行业的年轻人都搬到了上海。其中有一个男孩私底下偷偷告诉我,他真正搬离北京的原因是——“我不想在北京各位机构、前辈、大佬的脸色下生存,这太难了。”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他一句话,“你确定你到了上海,就没有大佬了吗?”


德国艺术家哈克(Hans Haacke)目前在纽约新美术馆举办的回顾性个展“All Connected”(全部相关)中,集中展示了他三十年来针对全球各地艺术生态的批评性研究。他惯用现场物和拼贴对艺术机制生产出的产品进行一种“建设性的挑衅”(productive provocation),加上一针见血的文字内容,反衬其中暗藏着的文化政治。他所批评的艺术机制包括美术馆、基金会、私人赞助人、双年展国家馆、文化宣传部门等。(图片由周婉京拍摄)
放眼全球,评奖机制决定“奖项从缺”?
反观大佬,他们就像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容易?大佬还觉得,自己又不是评了一个诺贝尔艺术奖(笔者建议瑞典人认真考虑一下设立此奖项)或英国特纳奖。明明昨晚还是后辈口中尊敬的“XXX老师”,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众矢之的”?或者就此问题,我们真正应该发问的是:华宇青年奖评委会大奖从缺,究竟惹怒了谁?一个奖项只要被运作出来,必然会经历的几个阶段,分别是:初评、复评、终评、宣布奖项、得奖者发表获奖感言。但同时还有一些我们不一定熟知的阶段,作为隐藏的环节没有浮出水面,例如:候选者放弃参评、评委争议、评委退出、奖项空缺、得奖者拒绝领奖、得奖者退还奖项、得奖者被爆有舞弊情节而撤销其所获奖项、奖项顺延至新的得奖者,等等。这样对比看来,华宇青年奖方才涉猎了“奖项空缺”和“得奖者拒绝奖项”两条新线索,很多人就已经按捺不住他们的情绪了。焦躁、愤怒、失落、担忧与悲伤一旦发作起来,对年轻艺术家自身才是最大的消耗。甚至太多人都来不及解决这一波的情绪问题,下一波的情绪又不停地涌了出来。如此一来,年轻艺术家在现存艺术生态当中的边缘化问题又会被情绪的问题所遮蔽。而事件的结果又是可预见性的残酷——国内艺术评奖机制最终通过暴露一些隐蔽的环节,进行了某种自我反省。同时,年轻艺术家对“空缺”的批评,反倒加固了这个奖项成立的合法性,让这个奖项受到关注并有了持续走下去的动因。倘若我们再大胆假设一下,同样的五位终审评委去评的是诺贝尔艺术奖,就一定不会出现“奖项从缺”的结果吗?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奖项本身隶属什么机构,它拥有的是怎样的调性。参照诺贝尔文学奖2019年的得奖情况——左右逢源、各个政治派别都不得罪的分羹方式——倒还不如给诺贝尔艺术奖一个“空缺”呢。面对全球政治局势日益分化的现状,诺贝尔文学奖同时颁给政治立场偏左翼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和曾经极右翼的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无疑是一种折中的对策,一个谁都不敢得罪的平庸之举。引用齐泽克(Žižek)的话来形容,“这个奖就应该在彼得·汉德克得到之后正式取消。”
2018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

2019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如果我们把反思的视野从华宇青年奖抽开,放到更广泛的全球视野,就会发现:真正出问题的也许不是国内评奖机制,而是全球政治局势下的评奖机制。今时今日,似乎无论你要评选什么奖,哪怕你是竞逐“酒仙桥小姐”都会遭到政界各方的审度与权衡。而在作出选择之时,每个人的每个动作看似与政治无关,却又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为了不沦为政治正确极有可能会滑向政治正确的反面——它不是“政治不正确”,而是以反对政治正确的立场建构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这样的评审过程,细细斟酌,可谓是“如坐针毡”。也就难怪2018年4月起三名负责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评委选择先后离开组委会。而在2019年12月,又有两名外部委员会成员宣布辞职,原因亦与汉德克获奖有关。评委忍不了得奖者的情况现在还没在国内艺术评奖体系中出现,但不排除将在不远的未来出现“评委罢评”的情况。
拒绝奖项的得奖者,能否成为下一个“萨特”?
值得思考的是,被人们记住的往往不是评委,而是那些退回奖项的得奖者。奖项越大,退回奖项的难度就越大,如此还坚持退回的人很难不成为“英雄”。萨特(Sartre)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曾在1964年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按照存在主义者萨特的逻辑,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那些“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而萨特本人是左翼自由主义(Left-libertarianism)知识分子,他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对右派的妥协,而拒绝它则是对原则的坚守。从这个意义上,他不能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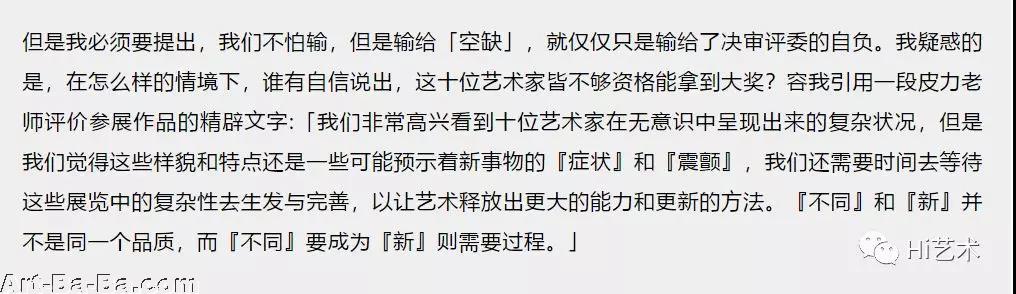
2019年华语青年奖“评委会特别奖”获奖者许哲瑜婉拒奖项后发表的回应文章《“空缺”之下的艺术家,与“空缺”之上的谁》片段
此刻再读一遍许哲瑜拒绝今届华宇青年奖的长文声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他拒绝的是评奖机制之下,作为创作者的“新”被视作“不同”(被形容成“症状”和“震颤”),而他认为“新”之所以无法自言其名是由于“新”此刻正经由一个根本上不认同“新”的评奖机制来判定,这个评奖机制自身就值得他怀疑。许哲瑜以拒绝奖项来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质上很值得认可。然而在这里,许哲瑜是否能够成为另一个“萨特”?他的拒绝是否就代表一种反抗资本与权力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奖项颁布之后再婉拒的方式是否依旧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有效的对抗?至于这些问题,都有待商榷。

纽约SoHo(苏豪区),位于曼哈顿

纽约TriBeCa(翠贝卡区),位于曼哈顿,房价昂贵,如今已是纽约贵族化社区的代表之一(该图片由周婉京拍摄)
最后回到那则“你确定你到了上海,就没有大佬了吗”的小故事。故事还有一个短短的续篇:年轻艺术家到了上海之后,他发现,上海有上海的问题,有些时候比北京还残酷。北京至少还遵循“艺术家中心化”的交友方式,不同代际的艺术家之间看人面、情面、场面,多少还会提携照顾一下。可到了上海,剧情急转直下,变成了“藏家中心化”的社交名利场。觥筹交错,置换的都是真金白银。故事的主人公,不得不经历新一轮的洗牌。后来,他听闻一个纽约艺术圈流传已久的笑话,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而且终将是一个无依无靠又渴望真情的浪荡儿。那个故事大概是说:“艺术家们没钱,他们刚开始住在SoHo,结果SoHo房价涨了。于是他们搬去了TriBeCa,结果TriBeCa房价也涨了。后来他们只能离开曼哈顿,去了布鲁克林,可是布鲁克林的房价竟然也涨了。最后,他们付不起房租,只好搬回家跟父母一起住了。”笔者写到这里,突发了一个奇想: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呼吁更多的地产商、实业家创办出更多的青年艺术家奖项。此外,在评奖之余,也请考虑一下给年轻人分套房子。留住他们,让他们暂且有个家,不用今晚就急着回家啃老。
注:2013年首届华宇青年奖大奖为20万元现金。2015年开始大奖奖励调整为5万元现金和25万元项目制作费。2019年华宇青年奖大奖空缺,不过比往年增加了一位特别奖获奖者。两位特别奖获奖者各得到3万元的现金奖励和25万元的项目制作费,空缺的大奖为5万元的现金奖励和25万元的项目制作费。